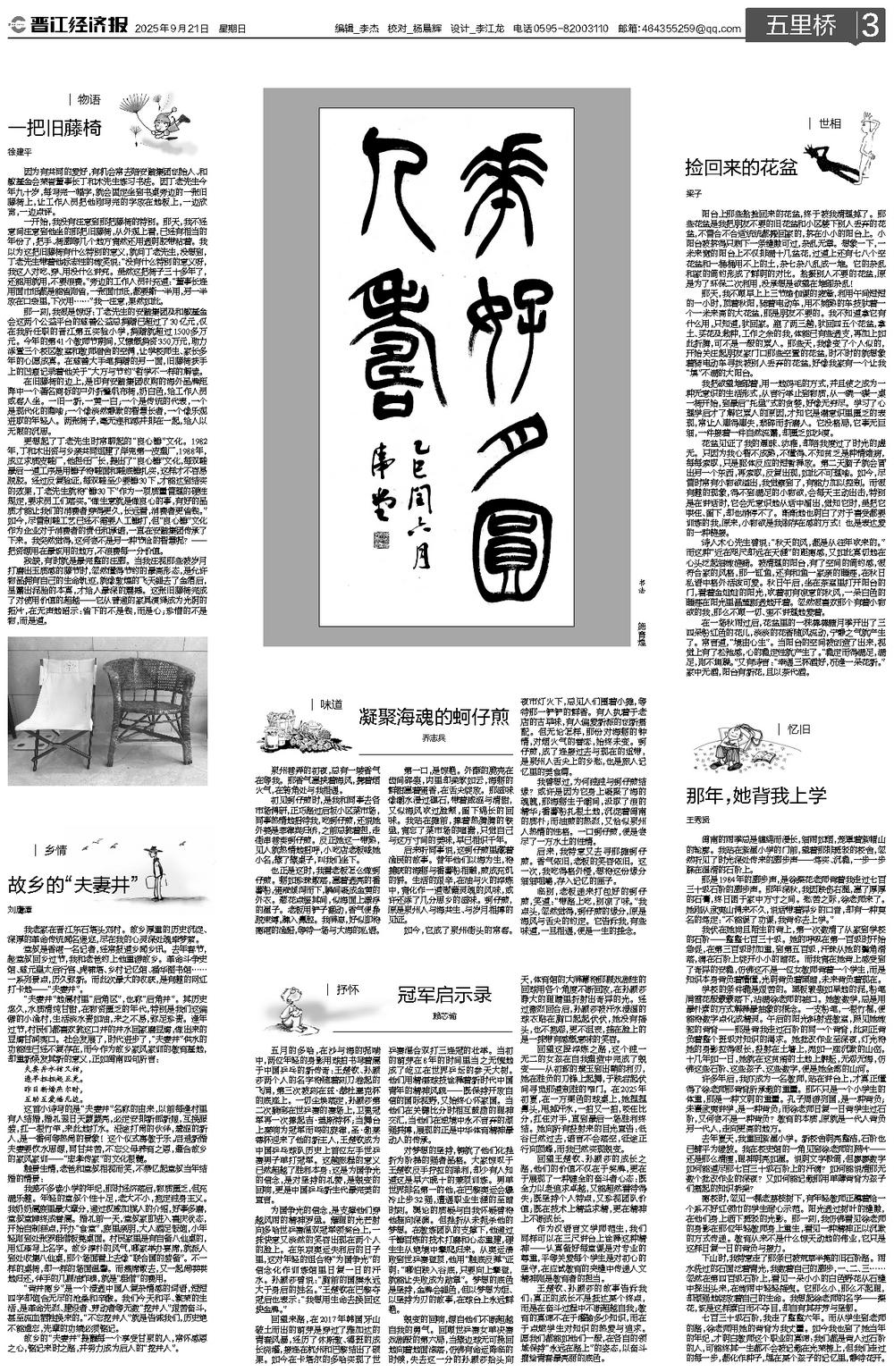王秀贤
闽南的雨季总是缠绵而漫长,细雨如烟,笼罩着紫帽山的轮廓。我站在紫星小学的门前,望着那排斑驳的校舍,忽然听见了时光深处传来的脚步声——笃实、沉稳,一步一步踩在湿滑的石阶上。
那是1984年的脚步声,是徐梨花老师背着我走过七百三十级石阶的脚步声。那年深秋,我因跌伤右腿,裹了厚厚的石膏,终日困于家中方寸之间。愁苦之际,徐老师来了。她刚从武夷山调来不久,说话带着异乡的口音,却有一种莫名的笃定:“不能误了功课,我背你去上学。”
我伏在她尚且陌生的背上,第一次数清了从家到学校的石阶——整整七百三十级。她的呼吸在第一百级时开始急促,在第三百级时加重,到第五百级,汗珠从她的鬓角滑落,滴在石阶上绽开小小的暗花。而我竟在她背上感受到了奇异的安稳,仿佛这不是一位女教师背着一个学生,而是知识本身背负着懵懂,光明背负着黑暗,未来背负着现在。
学校的条件确是艰苦的。黑板皲裂如旱地的泥,粉笔屑雪花般簌簌落下,沾满徐老师的袖口。她教数学,总是用最朴素的方式解释最抽象的概念。一支粉笔,一根竹棍,便能将数字点化成精灵。午后的阳光斜射进教室,照见她微驼的背脊——那是背我走过石阶的同一个背脊,此刻正背负着整个班级对知识的渴求。她批改作业至深夜,灯光将她的身影拉得很长,投射在土墙上,宛如一座沉默的山峦。十几年如一日,她就在这贫瘠的土地上耕耘,无怨无悔,仿佛这些石阶、这些孩子、这些数字,便是她全部的山河。
许多年后,我亦成为一名教师,站在讲台上,才真正懂得了徐老师那背脊所承载的重量。那不只是一个小学生的体重,那是一种文明的重量。孔子周游列国,是一种背负;朱熹武夷讲学,是一种背负;而徐老师日复一日背学生过石阶,又何尝不是一种背负?教育的本质,原就是一代人背负另一代人,走向更高的地方。
去年夏天,我重回紫星小学。新校舍明亮整洁,石阶也已铺平为缓坡。我在校史馆的一角见到徐老师的照片——还是那么清瘦,眼神明亮如星。说明文字极简,但寥寥数字如何能道尽那七百三十级石阶上的汗滴?如何能说清那无数个批改作业的深夜?又如何能记载那用单薄背脊为孩子们搭起的知识桥梁?
离校时,忽见一棵老荔枝树下,有年轻教师正蹲着给一个系不好红领巾的学生耐心示范。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他们身上洒下斑驳的光影。那一刻,我仿佛看见徐老师的身影在那位年轻教师身上重生,看见一种精神正以沉默的方式传递。教育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它只是这样日复一日的背负与接力。
下山时,我特意走了那条已被荒草半掩的旧石阶路。雨水洗过的石面泛着青光,我数着自己的脚步,一、二、三……忽然在第四百级石阶上,看见一朵小小的白色野花从石缝中探出头来,在微雨中轻轻摇曳。它那么小,那么不起眼,却顽强地绽放着自己的生命。我想起徐老师的名字——梨花,该是这样素白而不夺目,却自有其芬芳与坚韧。
七百三十级石阶,我走了整整六年。而从学生到老师的路,徐老师用她的背脊为我丈量。如今我也到了她当年的年纪,才明白教师这个职业的真谛:我们都是背人过石阶的人,可能终其一生都不会被记载在光荣榜上,但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化作种子,埋在某个孩子的记忆里,静待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