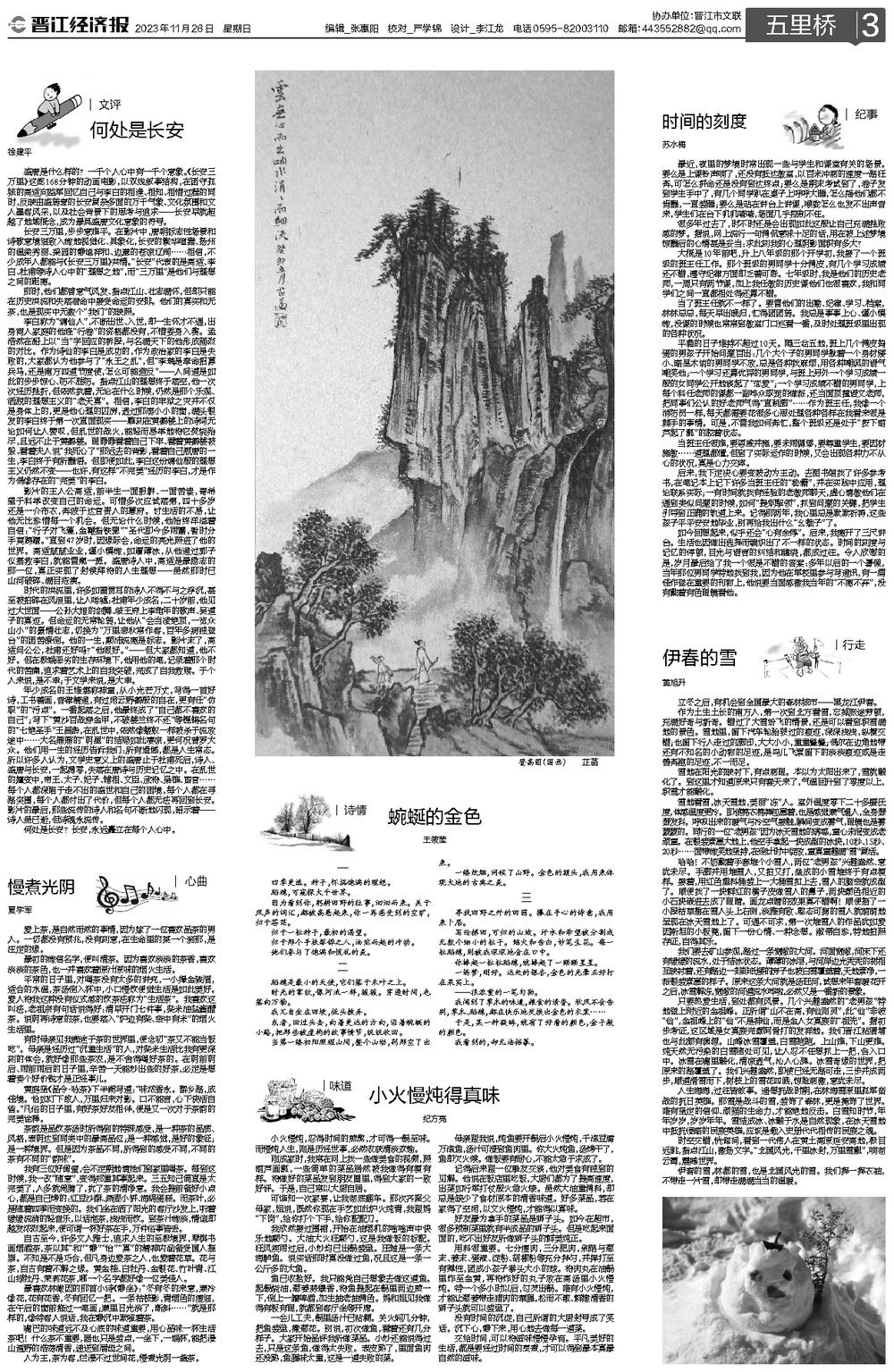徐建平
盛唐是什么样的?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意象。《长安三万里》这部168分钟的动画电影,以双线叙事结构,在困守孤城的高适向监军回忆自己与李白的相逢、相知、相惜过程的同时,反映由盛转衰的长安复杂多面的万千气象、文化氛围和文人墨客风采,以及社会背景下的思考与追求——长安早就超越了地域概念,成为最具盛唐文化意象的符号。
长安三万里,步步意难平。在影片中,唐朝标志性场景和诗歌意境细致入微地视觉化、具象化,长安的繁华喧嚣、扬州的温柔秀丽、梁园的静谧祥和、边塞的苍凉辽阔……相信,不少成年人都能与《长安三万里》共情。“长安”代表的是高适、李白、杜甫等诗人心中的“理想之地”,而“三万里”是他们与理想之间的距离。
那时,他们都曾意气风发、指点江山、壮志满怀,但却只能在历史洪流和失落宿命中接受命运的安排。他们的真实和无奈,也是现实中无数个“我们”的映照。
李白称为“谪仙人”,不断出世、入世,却一生怀才不遇,出身商人家庭的他连“行卷”的资格都没有,不惜委身入赘。孟浩然在船上以“当”字回应的桥段,与名满天下的他形成强烈的对比。作为诗仙的李白是成功的,作为政治家的李白是失败的,大家都认为他参与了“永王之乱”,但“李璘是奉命招募兵马,还是南方四道节度使,怎么可能造反”——人间道是如此的步步惊心、防不胜防。指点江山的理想终于落空,他一次次经历挫折,但依然执着,无论在什么时候,仍然是那个乐观、洒脱的理想主义的“老天真”。相信,李白的牢狱之灾并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他心理的囚房,透过那扇小小的窗,满头银发的李白终于第一次直面现实——雕刻在黄鹤楼上的诗词无论如何让人赞叹,但乱世的战火,能轻而易举地将它焚烧殆尽,且远不止于黄鹤楼。眼睁睁看着自己下牢、看着黄鹤楼被毁、看着夫人说“我死心了”那远去的背影,看着自己颓唐的一生,李白终于有所醒悟。但即便如此,李白这份谪仙般的理想主义仍然不变——也许,有这样“不完美”经历的李白,才是作为偶像存在的“完美”的李白。
影片的主人公高适,前半生一面躬耕、一面苦读,寄希望于科举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惜多次应试落第,四十多岁还是一介布衣,奔波于达官贵人的幕府。讨生活的不易,让他无比珍惜每一个机会。但无论什么时候,他始终洋溢着自信:“行子对飞蓬,金鞭指铁骢”“圣代即今多雨露,暂时分手莫踌躇。”直到47岁时,因缘际会,命运的亮光照进了他的世界。高适兢兢业业,谨小慎微,如履薄冰,从他通过郭子仪搭救李白,就能管窥一斑。盛唐诗人中,高适是最励志的那一位,真正实现了封侯拜将的人生理想——虽然那时已山河破碎、满目疮痍。
时代的洪流里,许多如雷贯耳的诗人不得不与之浮沉,甚至被拍碎在风浪里,让人唏嘘:杜甫年少成名,二十岁前,他见过大世面——公孙大娘的剑舞、岐王府上李龟年的歌声、吴道子的真迹。但命运的无常轮转,让他从“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壮志,切换为“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困苦潦倒。他的一生,颠沛流离是标志。影片末了,高适问公公,杜甫还好吗?“他很好。”——但大家都知道,他不好。但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他用他的笔,记录着那个时代的苦痛,追求着艺术上的自我突破,完成了自我救赎。于个人来说,是不幸;于文学来说,是大幸。
年少成名的王维堪称神童,从小光芒万丈,写得一首好诗,工书善画,音律精通,有过闲云野鹤般的自在,更有任“伪职”的“污点”。一番起落之后,他最终成了“自己都不喜欢的自己”;写下“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等铿锵名句的“七绝圣手”王昌龄,在乱世中,依然像蝼蚁一样被杀于流放途中……大名鼎鼎的“明星”的结局如此凄凉,更何况普罗大众。他们用一生的经历告诉我们:所有遗憾,都是人生常态。所以许多人认为,文学史意义上的盛唐止于杜甫死后,诗人、盛唐与长安,一起凋零,失落在唐诗与历史记忆之中。在乱世的嬗变中,帝王、太子、妃子、辅相、文臣、武将、枭雄、宦官……每个人都深陷于走不出的盛世和自己的困境,每个人都在寻路突围,每个人都付出了代价,但每个人都无法再回到长安。影片的最后,那些流传的诗人和名句不断地闪现,昭示着——诗人虽已逝,但诗魂永流传。
何处是长安?长安,永远矗立在每个人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