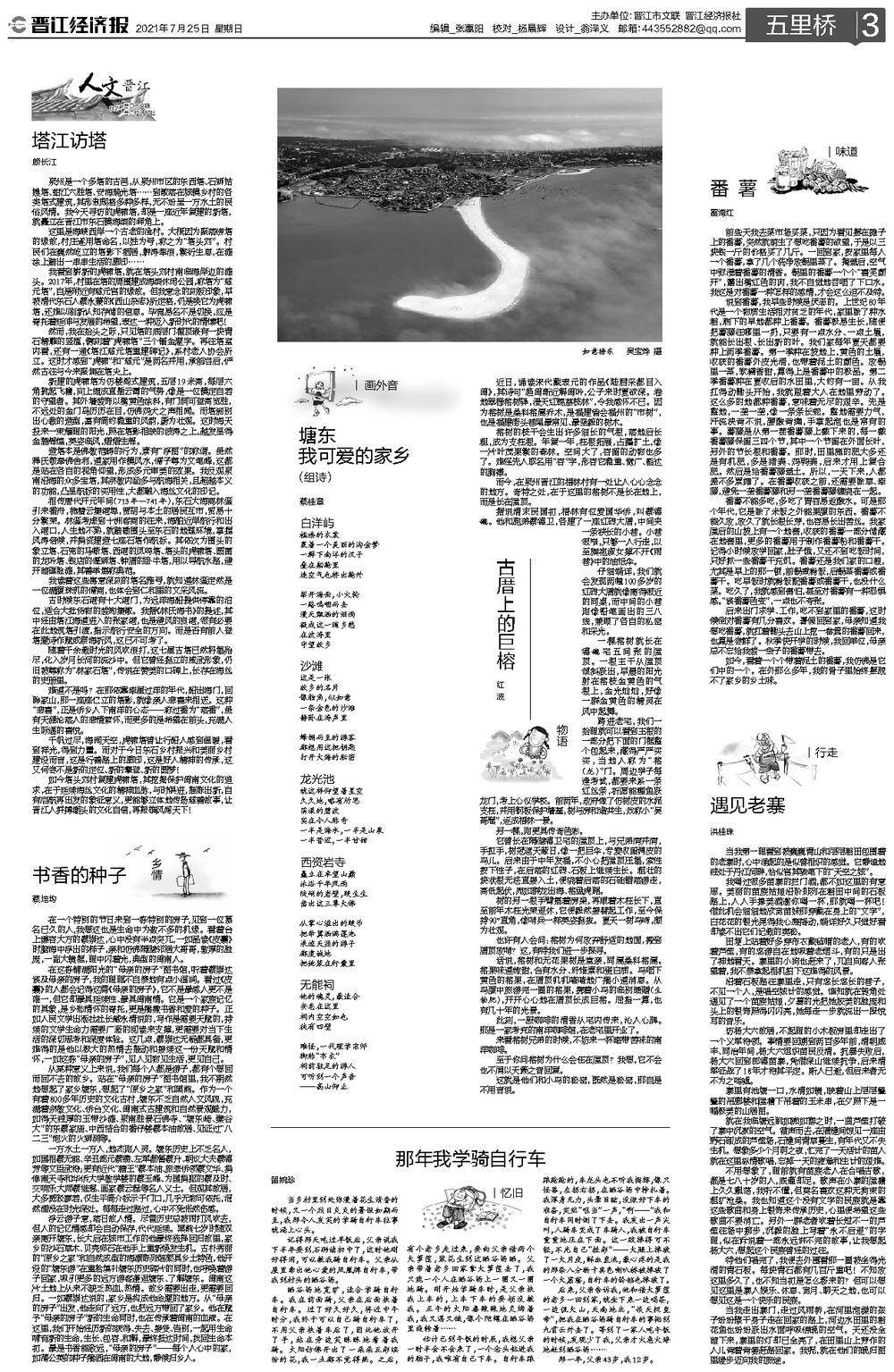雷海红
前些天我去菜市场买菜,只因为看见摆在摊子上的番薯,突然就萌生了想吃番薯的欲望,于是以三块钱一斤的价格买了几斤。一回到家,按家里每人一个番薯,拿了几个洗净放锅里蒸了。揭盖后,空气中弥漫着番薯的清香。锅里的番薯一个个“喜笑颜开”,露出橘红色的肉,我不自觉地吞咽了下口水。我这是对番薯一种怎样的感情,才会这么迫不及待。
说到番薯,我早些时候是厌恶的。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物质生活相对贫乏的年代,家里除了种水稻,剩下的旱地都种上番薯。番薯极易生长,随便把薯藤往哪里一扔,只要有一点水分、一点土壤,就能长出根、长出新的叶。我们家每年夏天都要种上两季番薯。第一季种在坡地上,黄色的土壤,收获的番薯外皮光滑,也带着泥土的颜色。放锅里一蒸,软糯香甜,算得上是番薯中的极品。第二季番薯种在夏收后的水田里,大约有一亩。从我扛得动锄头开始,我就跟着大人在地里劳动了。这么多的地都种番薯,意味着无尽的艰辛。先是整地,一垄一垄,像一条条长蛇。整地需要力气,汗流浃背不说,腰酸背痛,手掌起泡也是常有的事。薯藤是从第一茬番薯藤上截下来的,每一截番薯藤保留三四个节,其中一个节留在外面长叶,另外的节长根和番薯。那时,田里施的肥大多还是有机肥,多是猪粪、鸡鸭粪,后来才用上复合肥。然后是给番薯藤盖土。所以,一天下来,人都差不多累瘫了。在番薯收获之前,还需要除草、牵藤,避免一垄番薯藤和另一垄番薯藤缠绕在一起。
番薯不能多吃,多吃了胃容易返酸水。可是那个年代,它是除了米饭之外能果腹的东西。番薯不能久放,放久了就长根长芽,也容易长出苦丝。我家屋后的山坡上有一个地窖,收获的番薯一部分储藏在地窖里,更多的番薯用于制作番薯粉和番薯干。记得小时候放学回家,肚子饿,又还不到吃饭时间,只好抓一些番薯干充饥。番薯还是我们家的口粮,尤其是早上的那一顿,前锅煮稀饭,后锅蒸番薯或番薯干。吃早饭时就稀饭配番薯或番薯干,也没什么菜。吃久了,我就感到害怕,甚至对番薯有一种恐惧感。“谈番薯色变”,一点也不夸张。
后来出门求学、工作,吃不到家里的番薯,这时候倒对番薯有几分喜欢。暑假回到家,母亲知道我想吃番薯,就扛着锄头去山上挖一畚箕的番薯回来,也算是尝鲜了。秋季快开学的时候,我回单位,母亲总不忘给我装一袋子的番薯带去。
如今,看着一个个带着泥土的番薯,我仿佛是它们中的一个。在外那么多年,我的骨子里始终摆脱不了家乡的乡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