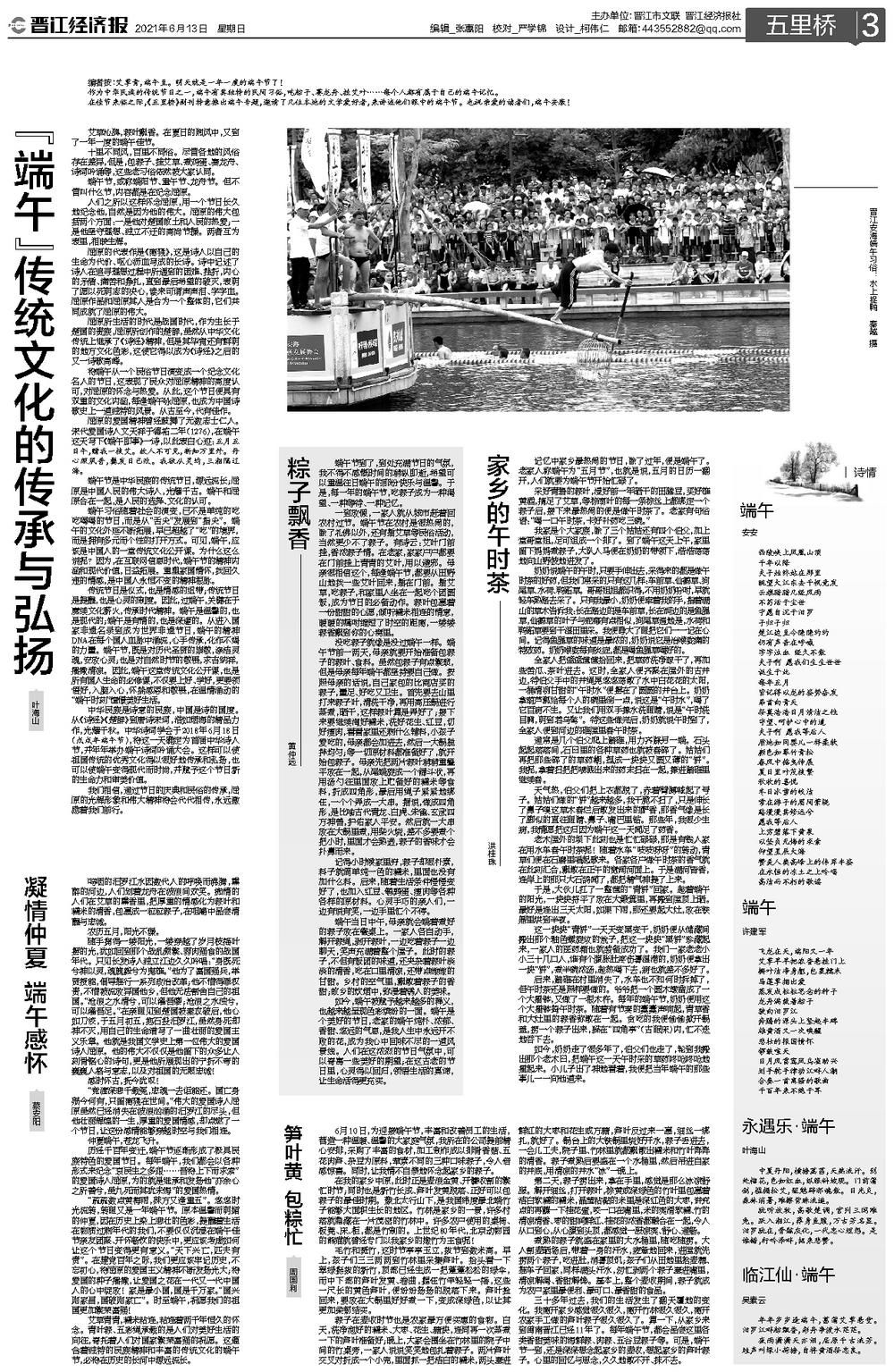记忆中家乡最热闹的节日,除了过年,便是端午了。老家人称端午为“五月节”,也就是说,五月的日历一翻开,人们就要为端午节开始忙碌了。
采好青碧的粽叶,浸好前一年晒干的田塍豆,买好雄黄酒,摘足了艾草,等棕扇叶的每一条棕丝上都绑定一个粽子后,接下来最热闹的便是做午时茶了。老家有句俗语:“喝一口午时茶,卡好补药吃三碗。”
我家是个大家族,除了三个姑姑还有四个伯父,加上堂哥堂姐,足可组成一个排了。到了端午这天上午,家里留下妈妈煮粽子,大队人马便在奶奶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向山野坡地进发了。
奶奶说端午的午时,只要手伸出去,采得来的都是做午时茶的好药,但我们常采的只有这几样:车前草、仙鹤草、狗尾草、水荷、鸭跖草。哥哥姐姐都识得,不用奶奶吩咐,早就轻车熟路去采了。只有我最小,奶奶便牵着我的手,指着满山的草木告诉我:长在路边的是车前草,长在涧边的是鱼腥草,仙鹤草的叶子与蛇莓有点相似,狗尾草遍地是,水荷和鸭跖草要到干湿田里采。我便睁大了眼把它们一一记在心间。记得鱼腥草的味道是最浓的,奶奶说它是治喉咙痛的特效药。奶奶喉咙每有炎症,都是喝鱼腥草喝好的。
全家人把篮篮筐筐抬回来,把草药洗净晾干了,再加些苦瓜、茶叶进去。这时,全家人便齐聚在屋外的古井边,待伯父手中的井绳晃悠悠荡散了水中白花花的太阳,一桶清冽甘甜的“午时水”便摆在了圆圆的井台上。奶奶拿葫芦瓢给每个人的碗里倒一点,说这是“午时水”,喝了它百病不生。又让我们用双手捧水洗眼睛,说是“午时洗目睭,明到若乌鹙”。待这些做完后,奶奶就说午时到了,全家人便到河边的碓屋里舂午时茶。
通常是几个伯父爬上踏碓,用力齐踩另一端。石头起起落落间,石臼里的各种草药也就被舂碎了。姑姑们再把那些碎了的草药糊,捏成一块块又圆又薄的“饼”。我呢,拿着扫把把喷溅出来的药末扫在一起,捧进踏碓里继续舂。
天气热,伯父们把上衣都脱了,赤着臂膊喊起了号子。姑姑们做的“饼”越来越多,我干脆不扫了,只是伸长了鼻子嗅这草木舂烂后散发出来的酽香,那香气像是长了脚似的直往眼睛、鼻子、嘴巴里钻。那些年,我很少生病,我情愿把这归因为端午这一天闻足了药香。
老木屋外的坝下此刻也是忙忙碌碌,那是有钱人家在用水车舂午时茶呢!随着水车“吱吱呀呀”的转动,青草们便在石磨里唱起歌来。各家各户做午时茶的香气就在此刻汇合,飘散在正午的宽阔河面上。于是满河皆香,连岸上的那只大石鸽闻了,都把精气神提了上来。
于是,大伙儿扛了一整筐的“青饼”回家。趁着端午的阳光,一块块捋平了放在大簸箕里,再搬到屋顶上晒。最好是连出三天太阳,如果下雨,那还要起大灶,放在铁鼎里烘到半夜。
这一块块“青饼”一天天变黑变干,奶奶便从储藏间搬出那个釉色螺旋纹的瓮子,把这一块块“黑饼”珍藏起来,一家人的医药箱也就装备成功了。我们一家老老小小三十几口人,谁有个腹胀肚疼伤暑湿滞的,奶奶便拿出一块“饼”,煮半碗浓汤,趁热喝下去,病也就差不多好了。
后来,踏碓在村里消失了,水车也不知何时拆掉了,但午时茶还是照样要做的。爷爷把一个圆木墩凿成了一个大擂钵,又做了一根木杵。每年的端午节,奶奶便用这个大擂钵捣午时茶。随着有节奏的橐橐声响起,青草香和大灶里的粽香弥散在一起。贪吃的我便偷偷掀开锅盖,捞一个粽子出来,躲在“四角亭”(古眠床)内,忙不迭地吞下去。
如今,奶奶走了很多年了,伯父们也走了,轮到我搬出那个老木臼,把端午这一天午时采的草药咚呛咚呛地擂起来。小儿子出了神地看着,我便把当年端午的那些事儿一一向他道来。
洪桂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