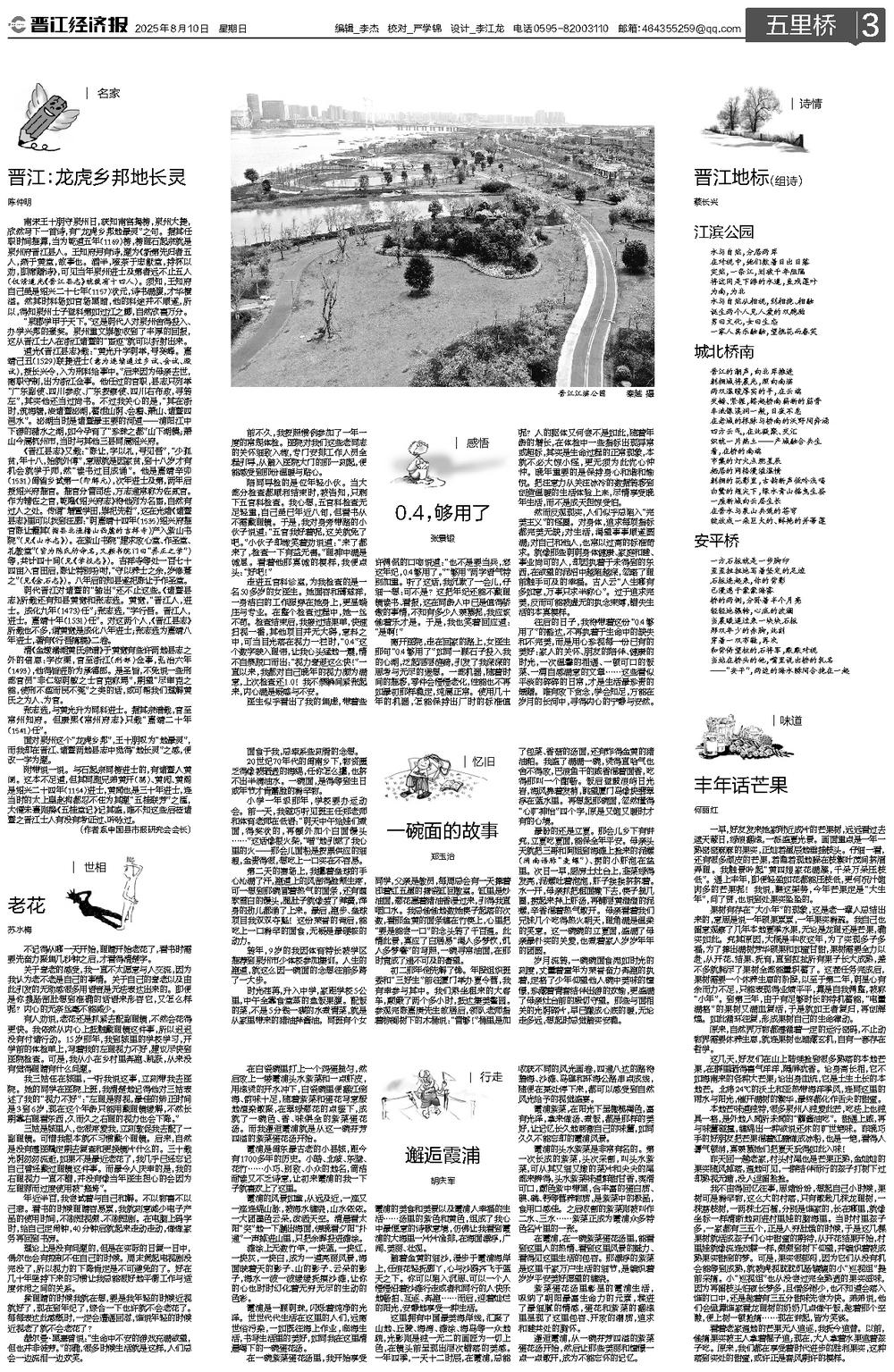郑玉治
面食于我,总牵系些刻骨的念想。
20世纪70年代的闽南乡下,物资匮乏得像被晒透的海绵,任你怎么攥,也挤不出半滴油水。一碗面,是得等到生日或年节才肯露脸的稀罕物。
小学一年级那年,学校要办运动会。前一天,我碰巧听见班主任郑老师和体育老师在低语:“明天中午给娃们煮面,得奖状的,再额外加个白面馒头……”这话像根火柴,“噌”地引燃了我心里的火——那会儿面粉是按票供应的细粮,金贵得很,想吃上一口实在不容易。
第二天的赛场上,我攥着垒球的手心沁满了汗,跑道上的风刮得脸颊生疼,可一想到那碗冒着热气的面条,还有暄软雪白的馒头,腿肚子就像装了弹簧,浑身的劲儿都涌了上来。最后,跑步、垒球项目我双双夺魁!这份荣誉的背后,能吃上一口稀罕的面食,无疑是最硬核的动力。
转年,9岁的我因体育特长被学区推荐到泉州市少体校参加集训。人生的跑道,就这么因一碗面的念想往前多跨了一大步。
时光荏苒,升入中学,家距学校5公里,中午全靠食堂蒸的盒饭果腹。配饭的菜,不是5分钱一碟的水煮青菜,就是从家里带来的猪油拌酱油。同班有个女同学,父亲是教员,每周总会有一天捧着印着红五星的搪瓷缸回教室。缸里是炒油面,葱花裹着猪油香漫过来,引得我直咽口水。我总偷偷地数她筷子起落的次数,看那金黄的面条缠在竹筷上,心里把“要是能尝一口”的念头转了千百遍。此情此景,真应了白居易“渴人多梦饮,饥人多梦餐”的写照,一碗寻常油面,在那时竟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初二那年倒先解了馋。年段组织班委和“三好生”前往厦门举办夏令营,我有幸参与其中。我们乘坐租来的大客车,颠簸了两个多小时,抵达集美鳌园。参观完陈嘉庚先生故居后,领队老师指着棕榈树下的木桶说:“管够!”桶里是加了包菜、香菇的汤面,还有炸得金黄的猪油粕。我盛了满满一碗,烫得直哈气也舍不得放,巴浪鱼干的咸香混着面香,吃得那叫一个酣畅。饭后登鼓浪屿日光岩,海风拂着发梢,眺望厦门岛像块翡翠浮在蓝水里。再想起那碗面,忽然懂得“心旷神怡”四个字,原是又饱又暖时才有的心境。
最盼的还是立夏。那会儿乡下有讲究,立夏吃夏面,能保全年平安。母亲头天就把三哥和阿姐到海滩上捡来的泥螺(闽南语称“麦螺”)、捞的小虾泡在盆里。次日一早,厨房土灶台上,韭菜绿得发亮,泥螺吐着泡泡,虾子挨挨挤挤着。水一开,母亲抓把粗面撒下去,筷子搅几圈,捞起来拌上虾汤,再铺层黄澄澄的泥螺,辛香混着热气散开。母亲看着我们兄妹几个吃得热火朝天,眼角满是温柔的笑意。这一碗碗的立夏面,盛满了母亲最朴实的关爱,也煮着家人岁岁年年的团圆。
岁月流转,一碗碗面食宛如时光的刻度,丈量着童年为荣誉奋力奔跑的执着,定格了少年仰望他人碗中美味的憧憬,珍藏着青春结伴出游的欢愉,更盛满了母亲灶台前的殷切守望。那些与面相关的光阴碎片,早已酿成心底的暖,无论走多远,想起时总觉踏实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