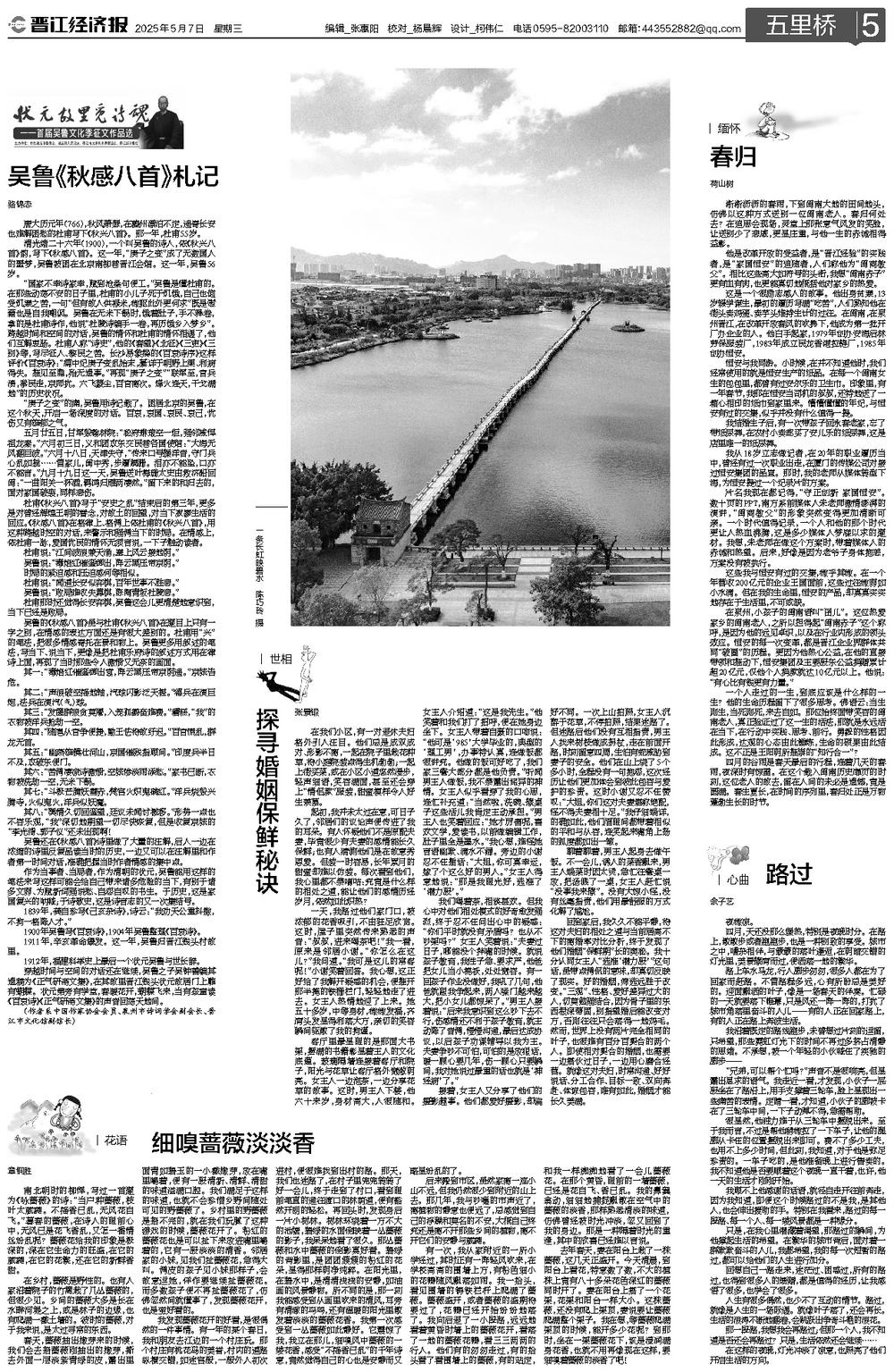骆锦恋
唐大历元年(766),秋风萧瑟,在夔州漂泊不定,遥寄长安也难解困愁的杜甫写下《秋兴八首》。那一年,杜甫55岁。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一个叫吴鲁的诗人,依《秋兴八首》韵,写下《秋感八首》。这一年,“庚子之变”成了无数国人的噩梦,吴鲁被困在北京南柳巷晋江会馆。这一年,吴鲁56岁。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吴鲁是懂杜甫的。在那些动荡不安的日子里,杜甫的小儿子死于饥饿,自己也饱受饥寒之苦,一句“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既是慰藉也是自我嘲讽。吴鲁在无米下锅时,饿着肚子,手不释卷,拿的是杜甫诗作,他说“杜陵诗编手一卷,再历饿乡入梦乡”。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对话,吴鲁的情怀和杜甫的情怀相遇了,他们互解衷肠。杜甫人称“诗史”,他的《春望》《北征》《三吏》《三别》等,写尽征人、黎民之苦。长沙易象撰的《百哀诗序》这样评价《百哀诗》:“篇中纪庚子变乱始末,綦详于朝野上栗、利病得失。推见至隐,殆无遗事。”再现“庚子之变”“联军至,官兵溃,拳民走,京师扰。六飞蒙尘,百官离次。烽火连天,干戈满地”的历史状况。
“庚子之变”的痛,吴鲁用诗记载了。困居北京的吴鲁,在这个秋天,开启一场深度的对话。百哀,哀国、哀民、哀己,忧伤又有雄郁之气。
五月廿五日,甘军毁翰林院:“秘府琳琅空一炬,强邻威悍祖龙秦。”六月初三日,义和团攻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大海无风翻巨波。”六月十八日,天津失守,“传来口号操洋音,守门兵心乱如搅……管家儿,闺中秀,步履蹒跚。泪亦不能坠,口亦不能言。”九月十九日这一天,吴鲁送叶梅珊太史由救济船回闽:“一曲阳关一杯酒,羁鸿归雁两凄然。”留下来的和归去的,面对家国破裂,同样悲伤。
杜甫《秋兴八首》写于“安史之乱”结束后的第三年,更多是对曾经辉煌王朝的眷念,对故土的回望,对当下寂寥生活的回应。《秋感八首》在格律上、格调上依杜甫的《秋兴八首》,用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来警示和强调当下的时局。在情感上,依杜甫一脉,爱国忧民的情怀无须言说,一下子触动读者。
杜甫说:“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吴鲁说:“毒焰红催銮御出,阵云黑压帝京阴。”
时局的紧迫感和压迫感何等相似。
杜甫说:“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
吴鲁说:“败局难收失算棋,陈陶青坂杜陵悲。”
杜甫那时还觉得长安弈棋,吴鲁这会儿更清楚地意识到,当下已经是败局。
吴鲁的《秋感八首》虽与杜甫《秋兴八首》在题目上只有一字之别,在情感的表达方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杜甫用“兴”的笔法,把很多情感寄托在景和物上。吴鲁更多用叙述的笔法,写当下、说当下,更像是把杜甫乐府诗的叙述方式用在律诗上面,再现了当时那些令人激愤又无奈的画面。
其一:“毒焰红催銮御出袁,阵云黑压帝京阴遥。”京城告危。
其二:“声浪破空摇地轴,汽球闪影泛天槎。”德兵在演巨炮,法兵在演汽(气)球。
其三:“发箧群狼贪莫餍,入笼孤鹤奋难费。”糟糕,“我”的衣物被洋兵抢劫一空。
其四:“随扈从官争便捷,勤王怯将故纡迟。”百官慌乱,群龙无首。
其五:“幽燕雄镇壮河山,京国催残指顾间。”印度兵半日不及,攻破东便门。
其六:“苦调凄凉诗激愤,空城惨淡雨添愁。”家书已断,衣物被洗劫一空,无米下锅。
其七:“斗极芒腾妖彗赤,梵宫火炽鬼磷红。”洋兵烧毁兴腾寺,火似鬼火,洋兵似妖魔。
其八:“舆情久切回銮望,廷议未闻讨檄移。”形势一点也不容乐观,“我”深切地期望一切尽快恢复,但是收复京城的“李光弼、郭子仪”还未出现啊!
吴鲁还在《秋感八首》诗里做了大量的注解,后人一边在浓缩的诗里反复品读当时的历史,一边又可以在注解里和作者第一时间对话,准确把握当时作者情感的集中点。
作为当事者、当局者,作为清朝的状元,吴鲁能用这样的笔法来写这样可能会给自己带来诸多危险的当下,有别于诸多文弱、为赋新词强说愁、自怨自叹的书生。于历史,这是家国复兴的呐喊;于诗歌史,这是诗言志的又一次集结号。
1839年,龚自珍写《己亥杂诗》,诗云:“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1900年吴鲁写《百哀诗》,1904年吴鲁整理《百哀诗》。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一年,吴鲁归晋江钱头村故里。
1912年,福建科举史上最后一个状元吴鲁与世长辞。
穿越时间与空间的对话还在继续,吴鲁之子吴钟善编其遗稿为《正气研斋文集》,在其故里晋江钱头状元故居门上雕有蝴蝶。状元第旁有学堂,春暖花开,蝴蝶飞来,当有孩童读《百哀诗》《正气研斋文集》的声音回荡天地间。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泉州市诗词学会副会长、晋江市文化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