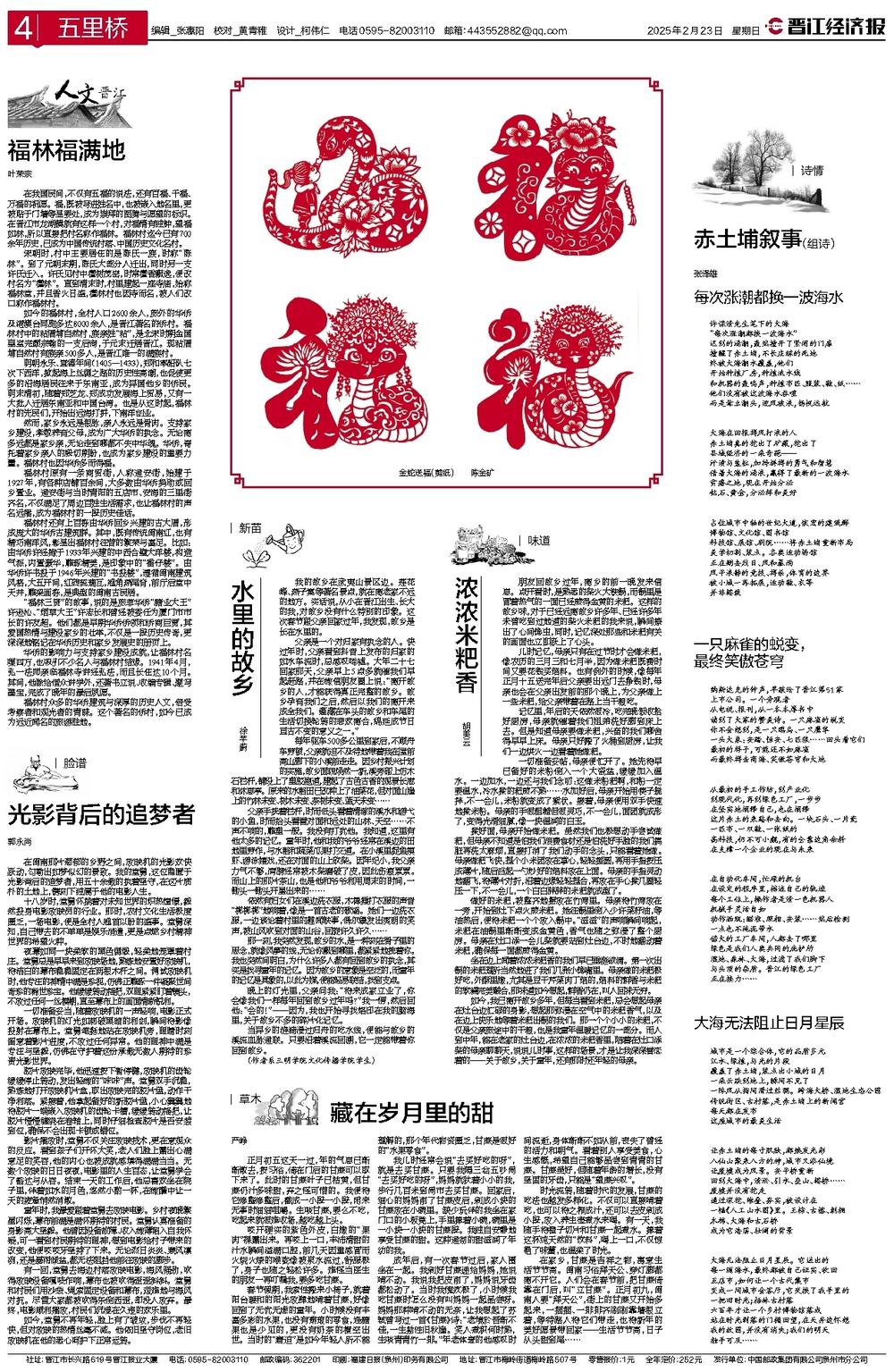胡美云
朋友回故乡过年,离乡的前一晚发来信息。点开看时,是熟悉的柴火大铁锅,而锅里是冒着热气的一面已经煎得金黄的米粑。这样的故乡味,对于已经远离故乡许多年、已经许多年未曾吃到过地道的柴火米粑的我来说,瞬间撩出了心间馋虫,同时,记忆深处那些和米粑有关的画面也立即跃上了心头。
儿时记忆,母亲只有在过节时才会做米粑,像农历的三月三和七月半,因为做米粑既费时间又要花钱买馅料。也有例外的时候,像每年正月十五送完年后父亲要出远门去挣钱时,母亲也会在父亲出发前的那个晚上,为父亲做上一些米粑,给父亲带着在路上当干粮吃。
记忆里,年后的天依然很冷,吃完晚饭收拾好厨房,母亲就催着我们姐弟洗好脚到床上去。但是知道母亲要做米粑,兴奋的我们哪舍得早早上床。母亲只好搬了火桶到厨房,让我们一边烘火一边看着她做粑。
一切准备妥帖,母亲便忙开了。她先将早已备好的米粉倒入一个大瓷盆,缓缓加入温水。一边加水,一边还与我们念叨:这做米粉粑啊,和粉一定要温水,冷水揉的粑煎不熟……水加好后,母亲开始用筷子搅拌,不一会儿,米粉就变成了絮状。接着,母亲便用双手快速地揉米粉。母亲的手很粗糙但很灵巧,不一会儿,面团就成形了,变得光滑细腻,像一块温润的白玉。
揉好面,母亲开始做米粑。虽然我们也极想动手尝试做粑,但母亲不知道是怕我们浪费食材还是怕洗好手脸的我们搞脏再洗太麻烦,直接打消了我们动手的念头,只能看着她做。母亲做粑飞快,捏个小米团放在掌心,轻轻搓圆,再用手指按压成薄片,随后舀起一勺炒好的馅料放在上面。母亲的手指灵动地翻飞,将薄片对折,沿着边缘轻轻捏合,再放在手心揉几圈轻压一下,不一会儿,一个白白胖胖的米粑就成型了。
做好的米粑,被整齐地摆放在竹筛里。母亲将竹筛放在一旁,开始到灶下点火煎米粑。她往锅里倒入少许菜籽油,等油热后,便将米粑一个个放入锅中。“滋滋”的声响瞬间响起,米粑在油锅里渐渐变成金黄色,香气也随之弥漫了整个厨房。母亲在灶口添一会儿柴就要站到灶台边,不时地翻动着米粑,确保每一面都煎得金黄。
坐在边上闻着浓浓米粑香的我们早已垂涎欲滴。第一次出锅的米粑理所当然地进了我们几张小馋嘴里。母亲做的米粑极好吃,外酥里嫩,尤其是豆干芹菜肉丁馅的,馅料的鲜香与米粑的软糯完美融合,那味道如今想起,鲜香仍在,叫人回味无穷。
如今,我已离开故乡多年,但每当看到米粑,总会想起母亲在灶台边忙碌的身影,想起那弥漫在空气中的米粑香气,以及在边上快乐地等着米粑出锅的我们。那一个个小小的米粑,不仅是父亲旅途中的干粮,也是我童年温暖记忆的一部分。而人到中年,能在老家的灶台边,在浓浓的米粑香里,陪着在灶口添柴的母亲聊聊天,说说儿时事,这样的场景,才是让我深深眷恋着的——关于故乡,关于童年,还有那时还年轻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