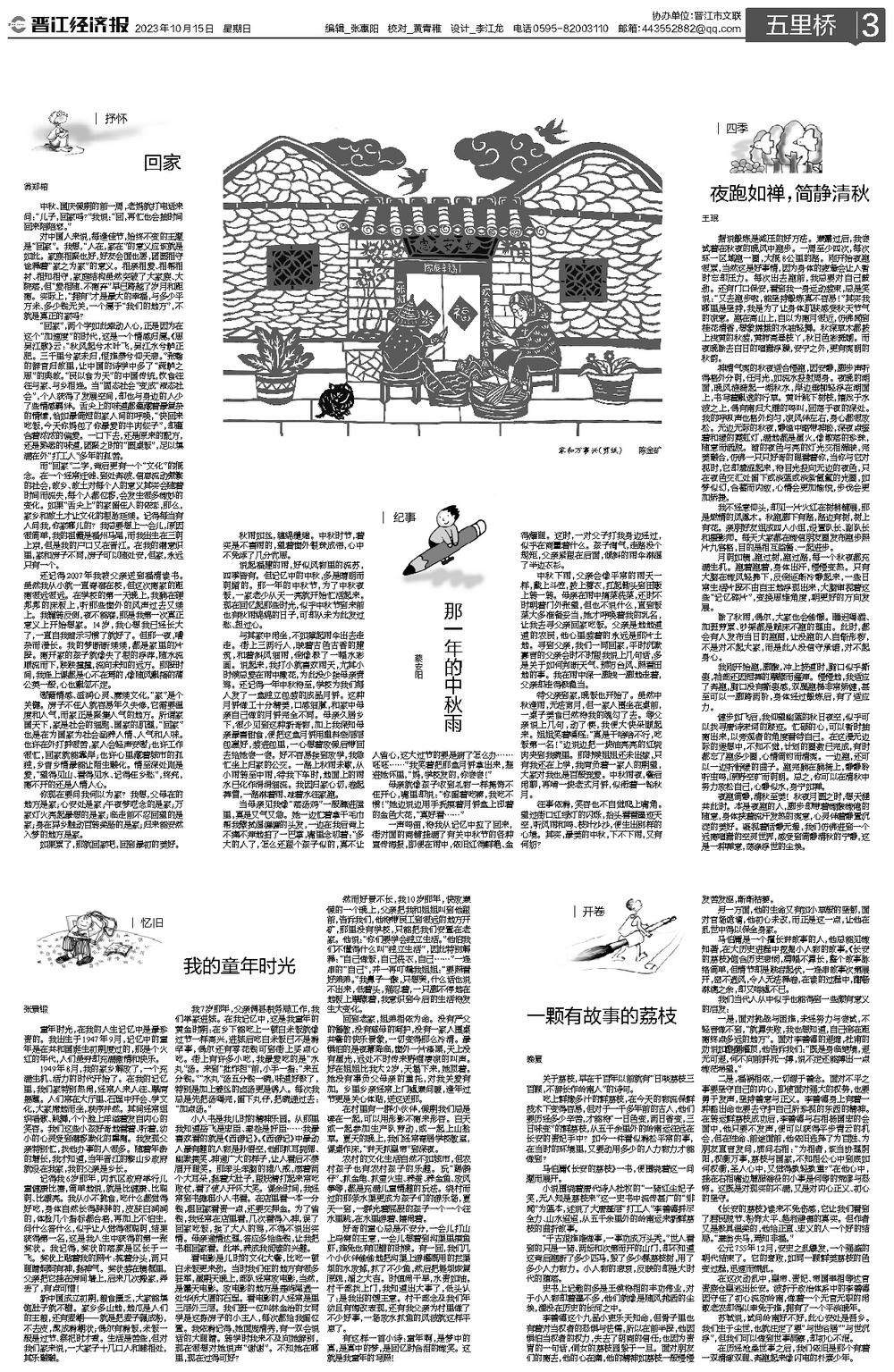翁郑榕
中秋、国庆假期的前一周,老妈就打电话来问:“儿子,回家吗?”我说:“回,再忙也会抽时间回来陪陪您。”
对中国人来说,每逢佳节,始终不变的主题是“回家”。我想,“人在,家在”的意义应该就是如此。家族相聚也好,好友会面也罢,团圆相守诠释着“家之为家”的意义。相亲相爱、相帮相衬、相知相守,家庭结构虽然突破了大家族、大院落,但“爱相随、不离弃”早已跨越了岁月和距离。实际上,“拥有”才是最大的幸福,与多少平方米、多少钱无关,一个属于“我们的地方”,不就是真正的家吗?
“回家”,两个字如此牵动人心,正是因为在这个“加速度”的时代,这是一个情感归属。《思吴江歌》云:“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张翰的辞官归故里,让中国的诗学中多了“莼鲈之思”的典故。“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传统,饮食往往与家、与乡相连。当“固态社会”变成“液态社会”,个人获得了发展空间,却也与身边的人少了些情感羁绊。舌尖上的味道都蕴藏着最复杂的情愫,恰如最简短的家人间的呼唤,“快回来吃饭,今天你妈包了你最爱的牛肉饺子”,却蕴含着浓浓的偏爱。一口下去,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团聚之时的“圆桌饭”,足以填满在外“打工人”多年的孤苦。
而“回家”二字,背后更有一个“文化”的概念。在一个经常迁徙、到处奔波、信息流动频繁的社会,故乡、故土对每个人的意义其实会随着时间而流失,每个人都位移,会发生很多微妙的变化。如果“舌尖上”的家留住人的依恋,那么,家乡和故土才让文化的根脉延续。记得每当有人问我,你家哪儿的?我总要想上一会儿,原因很简单,我的祖籍是福州马尾,而我出生在三明上京,但是我的户口又在晋江。在我的潜意识里,家和房子不同,房子可以随处安,但家,永远只有一个。
还记得2007年我被父亲送到福清读书。虽然我从小就一直寄宿在校,但这次离家的距离很远很远。在学校的第一天晚上,我躺在硬邦邦的床板上,听那些窗外的风声过去又续上。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开始想家。14岁,我心想我已经长大了,一直自我暗示习惯了就好了。但那一夜,嘈杂而漫长。我的梦断断续续,都是家里的片段。离开家的孩子就像失了根的浮萍,随水流顺流而下,跌跌撞撞,流向未知的远方。那段时间,我连上课都是心不在焉的,像随风飘摇的蒲公英一般,心也飘忽不定。
慰藉情感、滋润心灵、赓续文化,“家”是个关键。房子不住人就容易年久失修,它需要温度和人气,而家正是聚集人气的地方。所谓家国天下,家是社会的细胞、国家的肌理,“回家”也是在为国家为社会涵养人情、人气和人味。也许在外打拼很苦,家人会轻声安慰;也许工作很忙,回家就能靠岸;也许心里藏着城市的孤独,乡音乡情最能让陌生融化。情至深处则是爱,“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终究,离不开的还是人情人心。
你现在要问我何以为家?我想,父母在的地方是家;心安处是家;午夜梦呓念的是家;万家灯火亮起最想的是家;临走前不忍回望的是家;身在异乡触动百转柔肠的是家;归来能安然入梦的地方是家。
如果累了,那就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