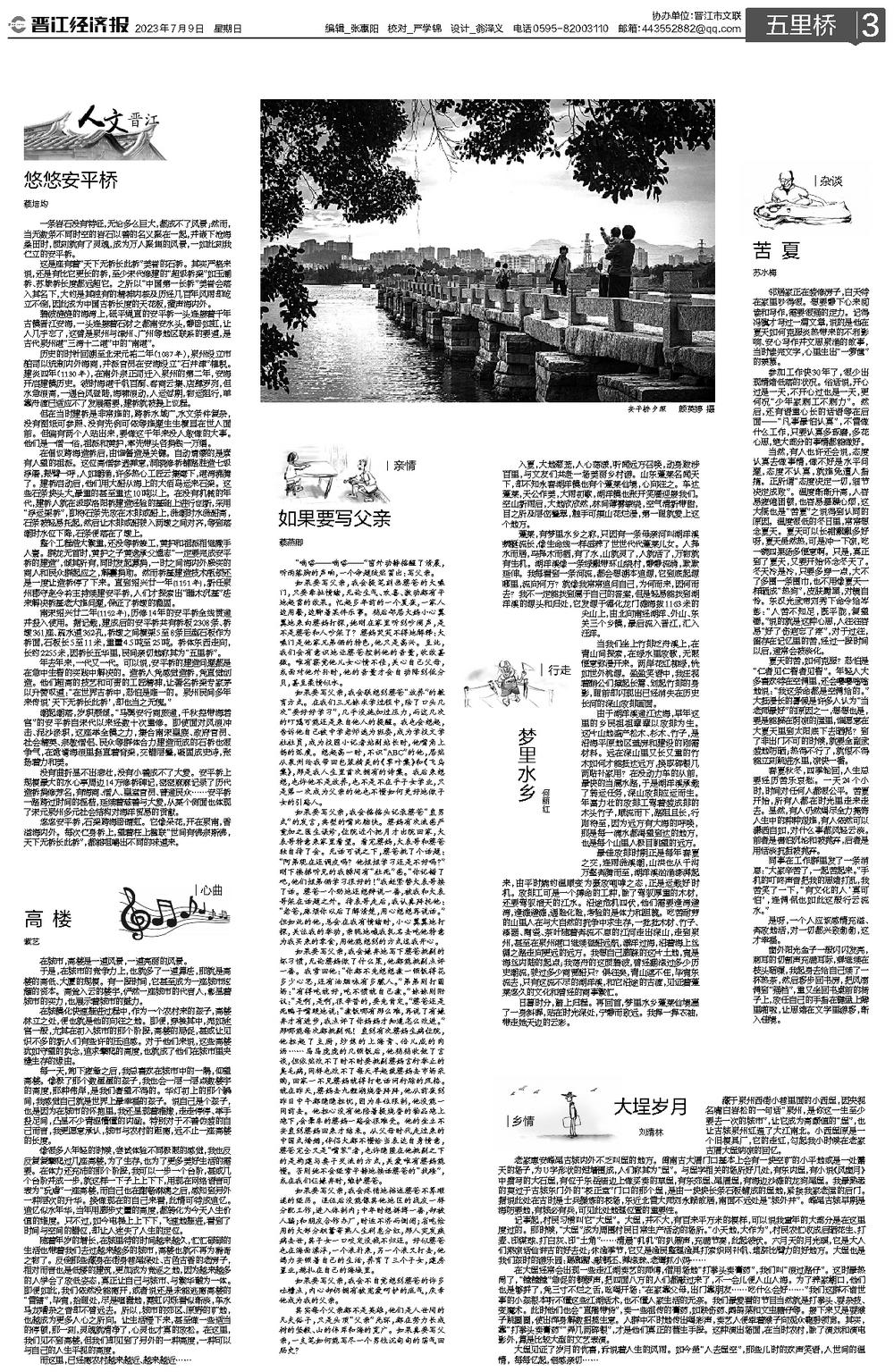蔡燕卿
“嘀嗒——嘀嗒——”窗外动静摇醒了清晨,听雨落脚的声响,一个命题陡然冒出:写父亲。
如果要写父亲,我会提笔刻画蔡爸的大嗓门,只要牵扯情绪,无论生气、欢喜、激动都有平地起雷的效果。忆起多年前的一个夏夜,一家人边用餐,边聊着某件乐事。稍后邻居大妈小心翼翼地来向蔡妈打探,她刚在家里听到吵闹声,是不是蔡爸和人吵架了?蔡妈哭笑不得地解释:大嗓门是他家兄弟俩的特色,他只是高兴。至此,我们会有意识地让蔡爸控制他的音量,收效甚微。唯有察觉他儿女心情不佳,关心自己父母,或面对他外孙时,他的音量才会自动降到低分贝,甚至柔情似水。
如果要写父亲,我会联想到蔡爸“放养”的教育方式。在我们三兄妹求学过程中,除了口头几次“要好好学习”,几乎没施加过压力,而这几次的叮嘱可能还是来自他人的提醒。我也会想起,告诉他自己被中学老师选为班委,成为学校文学社社员,成为校园小记者站副站长时,他嘴角上扬的弧度。想起高一时,不识“ABC”的他,居然从泉州给我带回包装精美的《草叶集》和《飞鸟集》,那是我人生里首次拥有的诗集。我后来想想,也许他不是放养,也不是不在乎子女学业,只是第一次成为父亲的他也不懂如何更好地做子女的引路人。
如果要写父亲,我会摇摇头记录蔡爸“直男式”的发言,典型的嘴比脑快。蔡妈有次流感严重加之医生误诊,住院近个把月才出院回家,大表哥特意来家里看望。看完蔡妈,大表哥和蔡爸独自待了会。无话可说之下,蔡爸挑了个话题:“阿弟现在还调皮吗?他姐姐学习还是不好吗?”刚下楼梯听见的我瞬间有“社死”感。“你记错了吧,他们姐弟俩学习很好的!”我赶紧替大表哥接了话。蔡爸一个劲地还想辩说一番,被我和大表哥架在话题之外。待表哥走后,我认真拜托他:“老爸,麻烦你以后了解清楚,用心想想再说话。”但如此的他,总会在我有情绪时,小心翼翼地打探,关注我的举动,亲昵地喊我乳名去吃他特意为我买来的零食,用他能想到的方式逗我开心。
如果要写父亲,我会嫌弃地写下蔡爸挑剔的坏习惯,无论蔡妈做了什么菜,他都能挑剔点评一番。我常回他:“你都不先想想煮一顿饭得花多少心思,还有油烟味有多腻人。”弟弟则打圆场:“有得吃就好,吃不惯就自己煮。”妹妹则附议:“是啊,是啊,很辛苦的,要先肯定。”蔡爸还是死鸭子嘴硬地说:“煮饭哪有那么难,再说了有嫌弃才有进步,我点评了你妈妈才知道怎么改进。”那哪能每次都挑剔呢!直到有次蔡妈生病住院,他担起了主厨,炒焦的上海青、倍儿咸的肉汤……马马虎虎的几顿饭后,他稍稍收敛了言谈,但依然改不了时不时要挑剔蔡妈言行举止的臭毛病,同样也改不了每天早起载蔡妈去市场采购,回家一不见蔡妈就得打电话问行踪的风格。就在昨天,蔡妈去九鲤湖烧香拜拜,他从前夜到昨日中午都隐隐担忧,因为车位限制,他没能一同前去。他担心没有他陪着提烧香的物品跑上跑下,会晕车的蔡妈一路会很难受。他的坐立不安直到蔡妈回来才结束。从父母时代走过来的中国式婚姻,伴侣大都不懂恰当表达自身情意,蔡爸完全又是“嘴笨”者,也许隐匿在他挑剔之下的是构建与妻子交流的方式,关爱唯有蔡妈能懂。否则她不会经常平静地接话蔡爸的“找碴”,或在我们仨嫌弃时,维护蔡爸。
如果要写父亲,我会疼惜地描述蔡爸不算顺遂的经历。退伍后没能像其他地区的战友一样分配工作,进入体制内;中年时想拼搏一番,却被人骗;和朋友合作办厂,时运不济而倒闭;省吃俭用的大部分积蓄寄熟人生利息分红,那人突发疾病去世,其子女一口咬定没钱不归还。好似蔡爸也在海面漂浮,一个浪扑来,另一个浪又打去,他竭力安顿着自己的生活,养育了三个子女,建房置业,稳扎在自己的海域里。
如果要写父亲,我会不自觉想到蔡爸的许多吐槽点,内心却仍拥有被宠爱呵护的底气,庆幸他成为我的父亲。
其实每个父亲都不是英雄,他们是人世间的凡夫俗子,只是头顶“父亲”光环,都在努力长成树的坚毅、山的伟岸和海的宽广。如果真要写父亲,一支笔如何能写尽一个男性沉甸甸的荡气回肠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