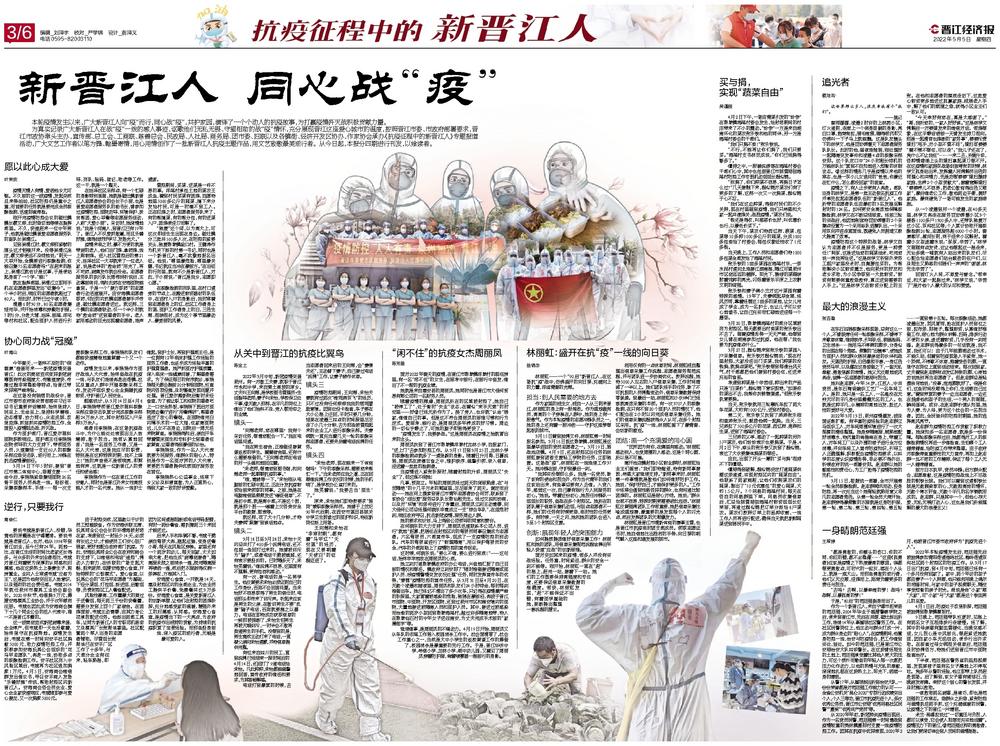陈金土
2022年3月中旬,新冠疫情突袭泉州。有一对教工夫妻,就职于晋江市永和中学,来自黄土高坡的原乡。丈夫叫王向辉,是学校图书管理员+生活指导老师;妻子叫朱怡,学校保卫处干事,像无数人那样,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他们始料不及、旁人敬而仰之的业绩。
镜头一
“向辉老师,您在哪里?我有个采访任务,想请您配合一下。”我在电话里问道。
“我在男生宿舍,正准备迎接复课返校的学生。看看宿舍里,还有什么需要准备的。”王向辉老师在电话的另一头温和地回应着。
“朱老师,想请您到图书馆,和向辉老师一起聊聊抗疫的事。”
“哦,请稍等一下。”朱怡刚从电脑前的忙碌中起立,正在分发抗疫物资给前来领取的同事。之前,她是在电脑微信里频频发送“催促信息”,不是初中部,就是高中部;不是这个班,就是那个班——催着上交各类安全平台的数据、图表等。
就这样,花了大十几分钟,才将夫妻俩“聚集”到谈话地点。
镜头二
3月18日至3月28日,朱怡十天内总共打了400多个流调电话,还不包括一些回打过来的。她曾被训斥为“骗子”,或者电话干脆被盖掉,还有表示要投诉的。已时隔多天了,朱怡笑着说:“做流调不容易,这里面有不理解,更有包容和感动。”
有一次,接电话的是一名男学生。他反复要求朱怡必须证明自己的工作身份,否则不会回答问题。当朱怡好不容易取得了男生的信任时,电话那头却传来了训斥声。听起来应该是男生的父亲,在教训男生不要“乱接”骗子电话,否则就要施之以暴力。电话在即将成功获取信息的一刹那被挂断了,朱怡生怕男生再被无端训斥,一时半会不敢再拨通男生的手机。没想到的是,男生竟然主动打来了电话,一直替父亲向朱怡道歉,并将信息提供完整。
有位来自四川的民工,直到流调已经结束一段时间后的4月14日,还回打了9通电话给朱怡。凡此种种,朱怡都能温馨地回答,宣传政府的做法和要求,为其答疑解惑。
电话打到最累的时候,去当志愿者回来后的王向辉,会“妻债夫还”,主动替下妻子,自己接过电话“流调”工作,让妻子稍作休息。
镜头三
疫情防控期间,王向辉、朱怡夫妻就有过两次“微雨燕双飞”的经历,只不过没有任何卿卿我我的烟雨朦胧意境。因到处设卡检查,车子要在大小公路上迂回,平时只要几分钟,结果在凌晨三四点的时间段里足足走了小几十分钟,去为那些被管控起来的企业工人进行核酸采样。夫妻俩就一直充当着几天一轮的核酸采样志愿者,还要夹杂着电话流调的任务。
镜头四
“朱怡老师,现在能来一下体育馆吗?下午的核酸采样,需要您来帮忙一下。”当朱老师应我之邀,正在回顾做流调工作状况的时候,她的手机响了,是学校办公室打来的。
她笑着说:“我要去当‘医生’了。”
原来,朱怡她们即将按要求“转岗”兼职核酸采样员。她曾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西安市蓝田县城关中学卫生班读过的医护知识,将在新岗位派上用场。
王向辉和朱怡在“非常时期”,都有着“马甲红”“天空蓝”的经历,现在又要朝着“天使白”的征程迈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