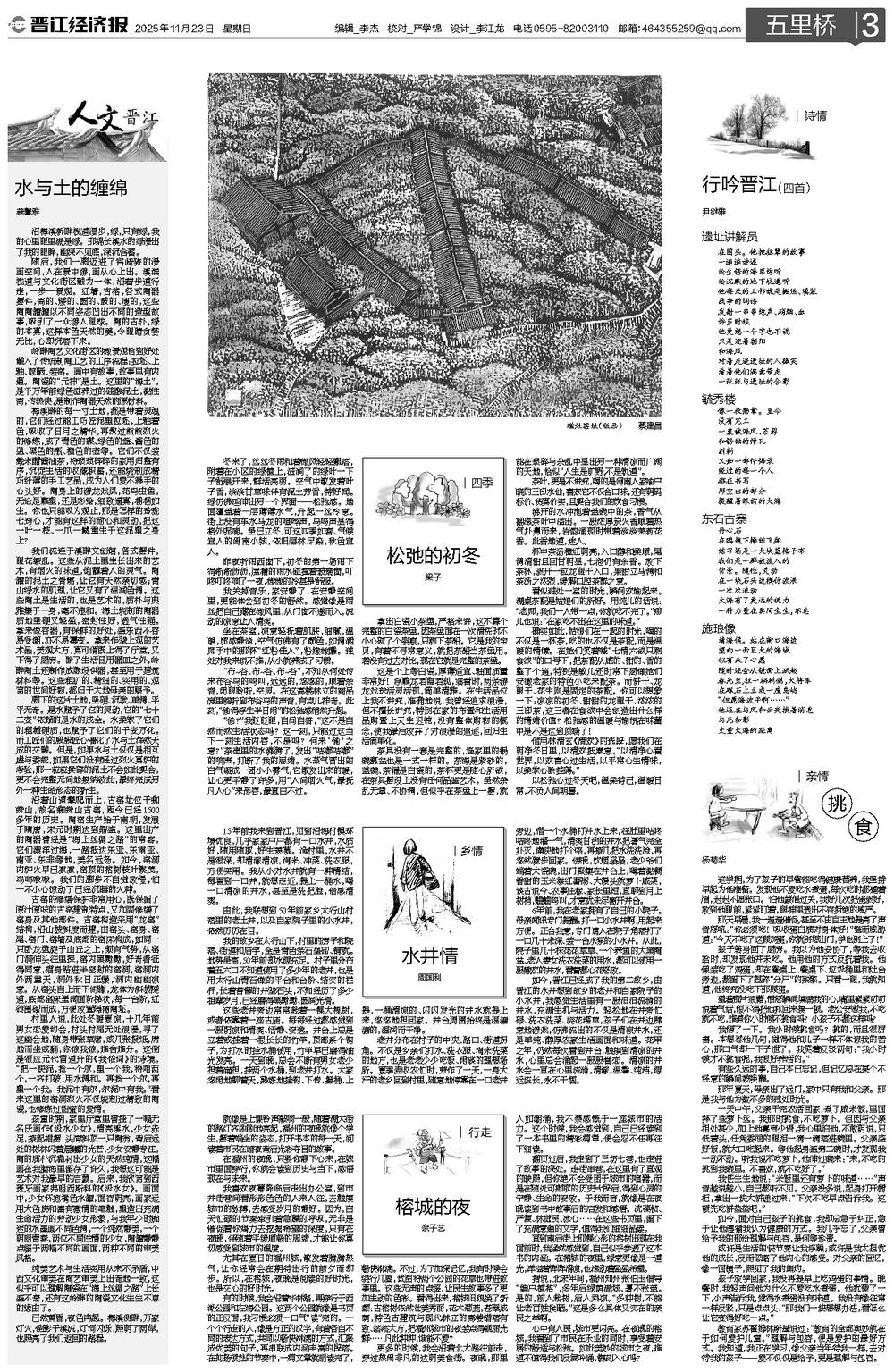杨菊华
这学期,为了孩子的早餐能吃得健康营养,我坚持早起为他准备。发现他不爱吃水煮蛋,每次吃时都蹙着眉,迟迟不愿张口。怕他蒙混过关,我好几次把蛋剥好,放到他眼前,紧紧盯着,眼神里透出不容拒绝的威严。
那天早晨,我一遍遍催促,甚至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声音怒吼:“你必须吃!吸收蛋白质对身体好!”继而威胁道:“今天不吃了这颗鸡蛋,你就别想出门,学也别上了!”
孩子转身回了厨房。我以为他妥协了,等我去收拾时,却发现他并未吃。他用他的方式反抗着我。他假装吃了鸡蛋,却在餐桌上、餐桌下、垃圾桶里和灶台旁边,都留下了捏碎“分尸”的残骸。只看一眼,我就知道,他终究没吃下那颗蛋。
望着那片狼藉,愤怒瞬间填满我的心,嘴里絮絮叨叨说着气话,恨不得把他抓回来揍一顿。老公安慰我,不吃就不吃,难道你小时候不挑食吗?小孩子不都这样吗?
我愣了一下。我小时候挑食吗?挑的,而且很厉害。本想怼他几句,觉得他和儿子一样不体谅我的苦心,那口气却一下子泄了。我笑着反驳两句:“我小时候才不挑食呢,我很好养活的。”
有些久远的事,自己本已忘记,但记忆总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被唤醒。
那年夏天,母亲出了远门,家中只有我和父亲。那是我与他为数不多的独处时光。
一天中午,父亲干完农活回家,煮了咸米饭,里面拌了些萝卜丝。我那时挑食,不吃萝卜。但因与父亲相处甚少,加上他寡言少语,我心里怕他,不敢明说,只低着头,任凭委屈的眼泪一滴一滴落进碗里。父亲盛好饭,就大口吃起来。等他起身盛第二碗时,才发现我一动不动。听我说不吃萝卜,他伸过碗来:“来,不吃的挑到我碗里。不喜欢,就不吃好了。”
我怯生生地说:“米饭里还有萝卜的味道……”声音越说越小,自己都听不见。父亲没多说,起身打开橱柜,拿出一块大饼递过来:“下次不吃早点告诉我。这顿先吃饼垫垫吧。”
如今,面对自己孩子的挑食,我却总急于纠正,急于让他遵循我认为健康的方式。我几乎忘了,父亲曾给予我的那份理解与包容,是何等珍贵。
或许是生活的快节奏让我浮躁;或许是我太担忧他的成长,反而忽略了他内心的感受。对父亲的回忆,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的焦灼。
孩子放学回家,我没再提早上吃鸡蛋的事情。晚餐时,我轻声问他为什么不爱吃水煮蛋。他犹豫了一下,小声告诉我,觉得水煮蛋没有味道。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反驳,只是点点头:“那我们一块想想办法,看怎么让它变得好吃一点。”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育的全部奥妙就在于如何爱护儿童。”理解与包容,便是爱护的最好方式。我知道,我正在学习,像父亲当年待我一样,去对待我的孩子——爱不仅仅是给予,更是理解与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