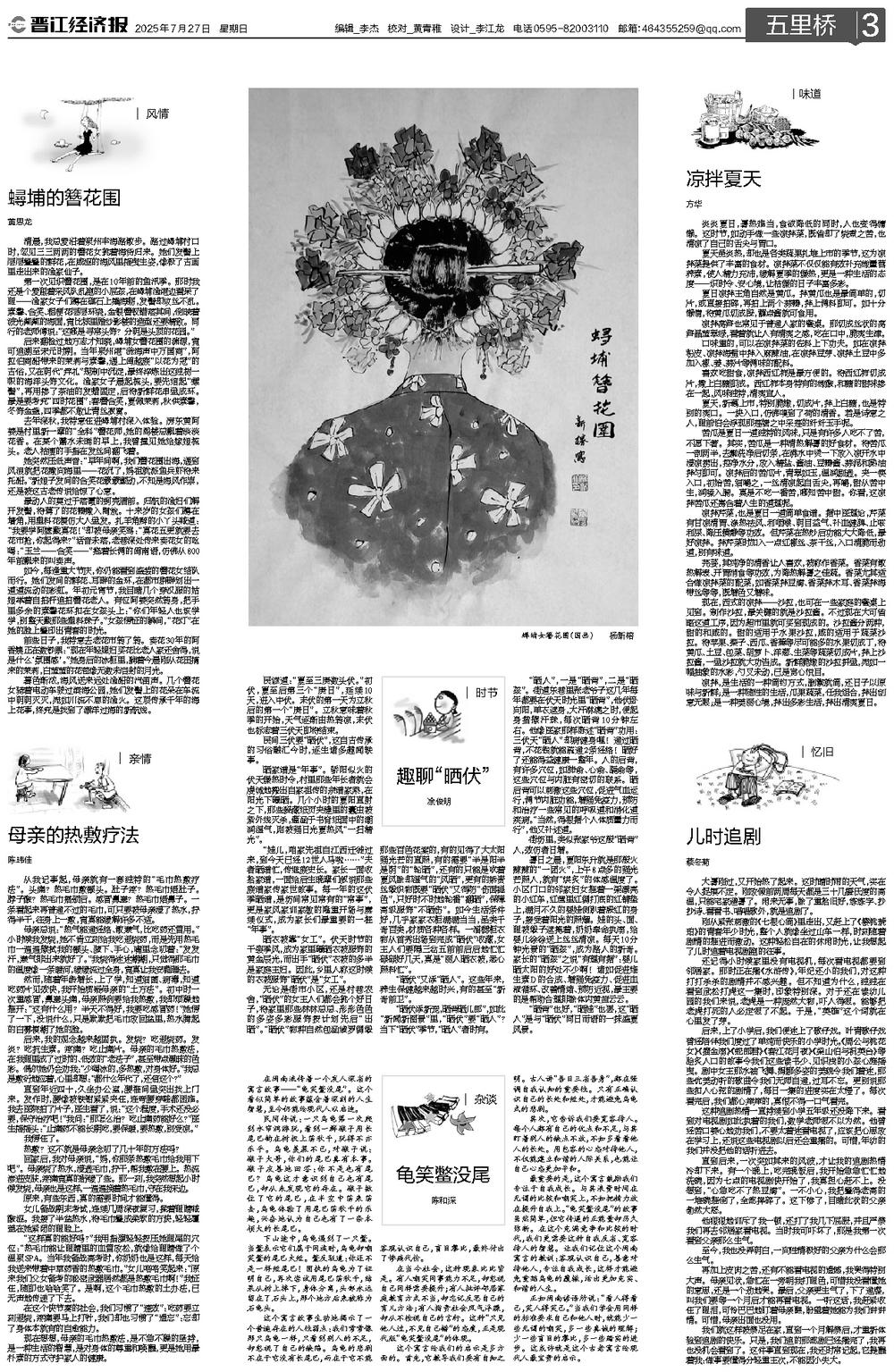陈玮佳
从我记事起,母亲就有一套独特的“毛巾热敷疗法”。头痛?热毛巾敷额头。肚子疼?热毛巾焐肚子。脖子酸?热毛巾搭颈后。感冒鼻塞?热毛巾焐鼻子。一条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毛巾,可只要被母亲浸了热水,拧得半干,往身上一敷,竟真能缓解许多不适。
母亲总说:“热气能通经络、散寒气,比吃药还管用。”小时候我发烧,她不肯立刻给我吃退烧药,而是先用热毛巾一遍遍擦拭我的额头、腋下、手心,嘴里念叨着:“发发汗,寒气排出来就好了。”我烧得迷迷糊糊,只觉得那毛巾的温度像一条暖河,缓缓流过全身,竟真让我安稳睡去。
然而,随着年龄增长,上了学,知道细菌、病毒,知道吃药片见效快,我开始质疑母亲的“土方法”。初中时一次重感冒,鼻塞头痛,母亲照例要给我热敷,我却烦躁地推开:“这有什么用?半天不得好,我要吃感冒药!”她愣了一下,没说什么,只是默默把毛巾放回盆里,热水腾起的白雾模糊了她的脸。
后来,我的观念越来越固执。发烧?吃退烧药。发炎?吃抗生素。疼痛?吃止痛片。母亲的毛巾热敷法,在我眼里成了过时的、低效的“老法子”,甚至带点愚昧的色彩。偶尔她仍会劝我:“少喝冰的,多热敷,对身体好。”我总是敷衍地应着,心里却想:“都什么年代了,还信这个?”
直到年近四十,久坐办公室,腰椎间盘突出找上门来。发作时,腰像被铁钳紧紧夹住,连弯腰穿鞋都困难。我去医院拍了片子,医生看了,说:“这个程度,手术还没必要,保守治疗吧!”我问:“那怎么治?吃止痛药能好么?”医生摇摇头:“止痛药不能长期吃,要保暖,要热敷,别受凉。”
我愣住了。
热敷?这不就是母亲念叨了几十年的方法吗?
回家后,我对母亲说,“妈,你那条热敷毛巾给我用下吧”。母亲烧了热水,浸透毛巾,拧干,帮我敷在腰上。热流渗进皮肤,疼痛竟真的舒缓了些。那一刻,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发烧,母亲也是这样,一遍遍换着热毛巾,守在我床边。
原来,有些东西,真的需要时间才能懂得。
女儿备战期末考试,连续几周深夜复习,揉着眼睛喊酸涩。我接了半盆热水,将毛巾叠成柔软的方块,轻轻覆盖在她紧闭的眼睑上。
“这样真的能好吗?”我用指腹轻轻按压她眼尾的穴位:“热毛巾能让眼睛里的血管放松,就像给眼睛做了个温泉SPA。当年我备战高考时,你奶奶也是这样,每天给我送来带着中草药香的热敷毛巾。”女儿咯咯笑起来:“原来我们父女备考的秘密武器居然都是热敷毛巾啊!”我怔住,随即也哈哈笑了。是啊,这个毛巾热敷的土办法,已无声地传递了下去。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我们习惯了“速效”:吃药要立刻退烧,疼痛要马上打针,我们却也习惯了“遗忘”:忘却了身体本就有的自愈能力。
现在想想,母亲的毛巾热敷法,是不急不躁的坚持,是一种生活的智慧,是对身体的尊重和唤醒,更是她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家人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