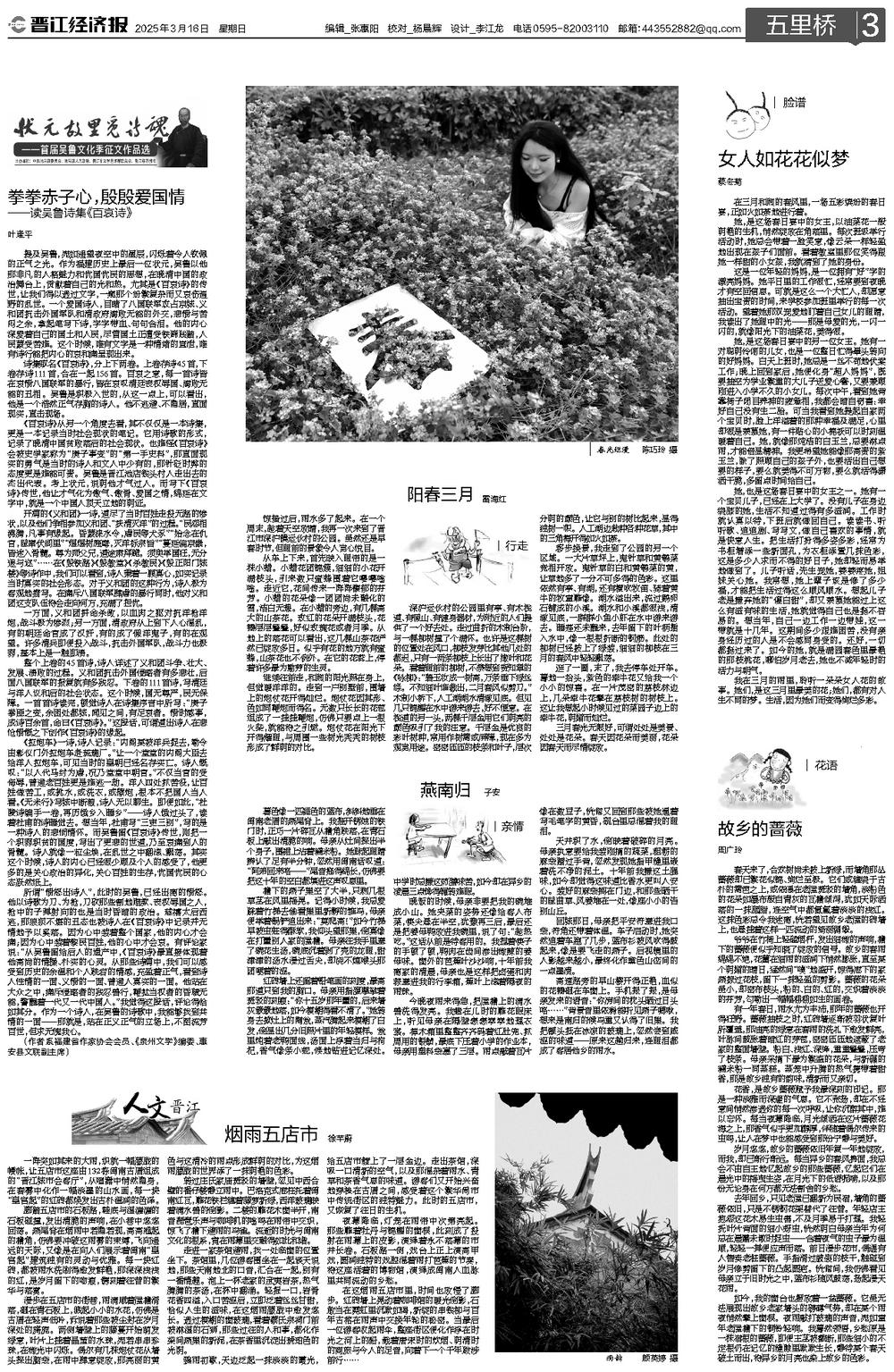叶逢平
提及吴鲁,宛如遥望夜空中的星辰,闪烁着令人钦佩的正气之光。作为福建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吴鲁以他那非凡的人格魅力和忧国忧民的思想,在晚清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贡献着自己的光和热。尤其是《百哀诗》的传世,让我们得以透过文字,一窥那个纷繁复杂而又哀伤遍野的乱世。一个爱国诗人,目睹了八国联军攻占京城、义和团抗击外国军队和清政府腐败无能的外交,悲愤与苦闷之余,拿起笔写下诗,字字带血、句句含泪。他的内心深爱着自己的国土和人民,尽管国土正遭受铁蹄践踏,人民蒙受苦难。这个时候,唯有文字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唯有诗行能把内心的哀和痛呈现出来。
诗集取名《百哀诗》,分上下两卷。上卷存诗45首,下卷存诗111首,合在一起156首。百哀之意,每一首诗皆在哀愤八国联军的暴行,皆在哀叹清廷丧权辱国、腐败无能的丑相。吴鲁是积极入世的,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浩然正气存胸的诗人。他不逃避、不隐居,直面现实,直击现场。
《百哀诗》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其不仅仅是一本诗集,更是一本记录当时社会现状的笔记。它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了晚清中国贫败落后的社会现状。也难怪《百哀诗》会被史学家称为“庚子事变”的“第一手史料”,那直面现实的勇气是当时的诗人和文人中少有的,那针砭时弊的态度更是难能可贵。吴鲁是晋江池店钱头村人走出去的杰出代表。考上状元,说明他才气过人。而写下《百哀诗》传世,他让才气化为傲气、傲骨、爱国之情,绵延在文字中,就是一个中国人顶天立地的明证。
开篇的《义和团》一诗,道尽了当时百姓走投无路的惨状,以及他们争相参加义和团、“扶清灭洋”的过程。“民怨相沸腾,凡事有缘起。昏蒙涞水令,虐民等犬豕”“始念在仇官,鼠窜伏闾里”“煜煜树旌麾,灭洋标宗旨”“蔓延偏京畿,皆迷入骨髓。尊为师父兄,道途肃拜跪。须臾举国狂,无分遐与迩”……在《毁铁路》《毁教堂》《杀教民》《毁正阳门城楼》等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秉着一颗真心,如实记录当时真实的社会形态。对于义和团的这种行为,诗人极为客观地描写。在痛斥八国联军肆虐的暴行同时,他对义和团这支队伍将会走向何方,充满了担忧。
一方面,义和团拼命杀敌,以血肉之躯对抗洋枪洋炮,战斗极为惨烈;另一方面,清政府从上到下人心混乱,有的朝廷命官成了汉奸,有的成了假洋鬼子,有的在观望。许多清兵即便投入战斗,抗击外国军队,战斗力也极弱,基本上是一触即溃。
整个上卷的45首诗,诗人详述了义和团斗争、壮大、发展、溃败的过程。义和团抗击外国侵略者有多悲壮,后面八国联军的报复就有多残忍。下卷的111首诗,写清廷与洋人议和后的社会状态。这个时候,国无尊严,民无保障。一首首诗读完,顿觉诗人在诗集序言中所写:“庚子拳匪之变,余困处都城,闻见之间,有足哀者。愤时感事,成诗百余首,命曰《百哀诗》。”这段话,可谓道出诗人在悲怆愤慨之下创作《百哀诗》的缘起。
《拉炮车》一诗,诗人记录:“内阁某被洋兵捉去,勒令由彰仪门外拉炮车赴琉璃厂。”让一个堂堂的内阁大臣去给洋人拉炮车,可见当时的皇朝已经名存实亡。诗人慨叹:“以人代马纣为虐,况乃堂堂中朝官。”不仅当官的受侮辱,普通老百姓更是难逃一劫。洋人四处抓苦役,让百姓做苦工,或挑水,或洗衣,或擦炮,根本不把国人当人看。《无米行》写城中断粮,诗人无以聊生。即便如此,“杜陵诗编手一卷,再历饿乡入睡乡”——诗人饿过头了,读着杜甫的诗睡觉去。想当年,杜甫写“三吏三别”,写的是一种诗人的悲悯情怀。而吴鲁留《百哀诗》传世,则把一个积弱积贫的国度,写出了更悲的世道,乃至哀痛到人的骨髓。诗人就像一粒尘埃,在乱世之中翻滚、飘荡。其实这个时候,诗人的内心已经很少顾及个人的感受了,他更多的是关心政治的异化,关心百姓的生存,忧国忧民的心态跃然纸上。
所谓“愤怒出诗人”,此时的吴鲁,已经出离的愤怒。他以诗歌为刀、为枪,刀砍那些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人,枪中的子弹射向的也是当时昏暗的政治。慈禧太后西逃,那狼狈不堪的丑态也被诗人在《百哀诗》中记录并无情地予以奚落。因为心中装着整个国家,他的内心才会痛;因为心中装着黎民百姓,他的心中才会哀。有评论家说:“从吴鲁留给后人的遗产中,《百哀诗》最直接体现着他高尚的情操、朴实的心灵。从那些诗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的余温和个人跌宕的情感,充盈着正气,看到诗人性情的一面、义愤的一面、普通人真实的一面。他站在大众之中,痛斥侵略者的残忍兽行,鞭挞当权者的昏聩无能,警醒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我觉得这段话,评论得恰如其分。作为一个诗人,在吴鲁的诗歌中,我能够找到共情的一面——那就是,站在正义正气的立场上,不图流芳百世,但求无愧我心。
(作者系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泉州文学》编委、惠安县文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