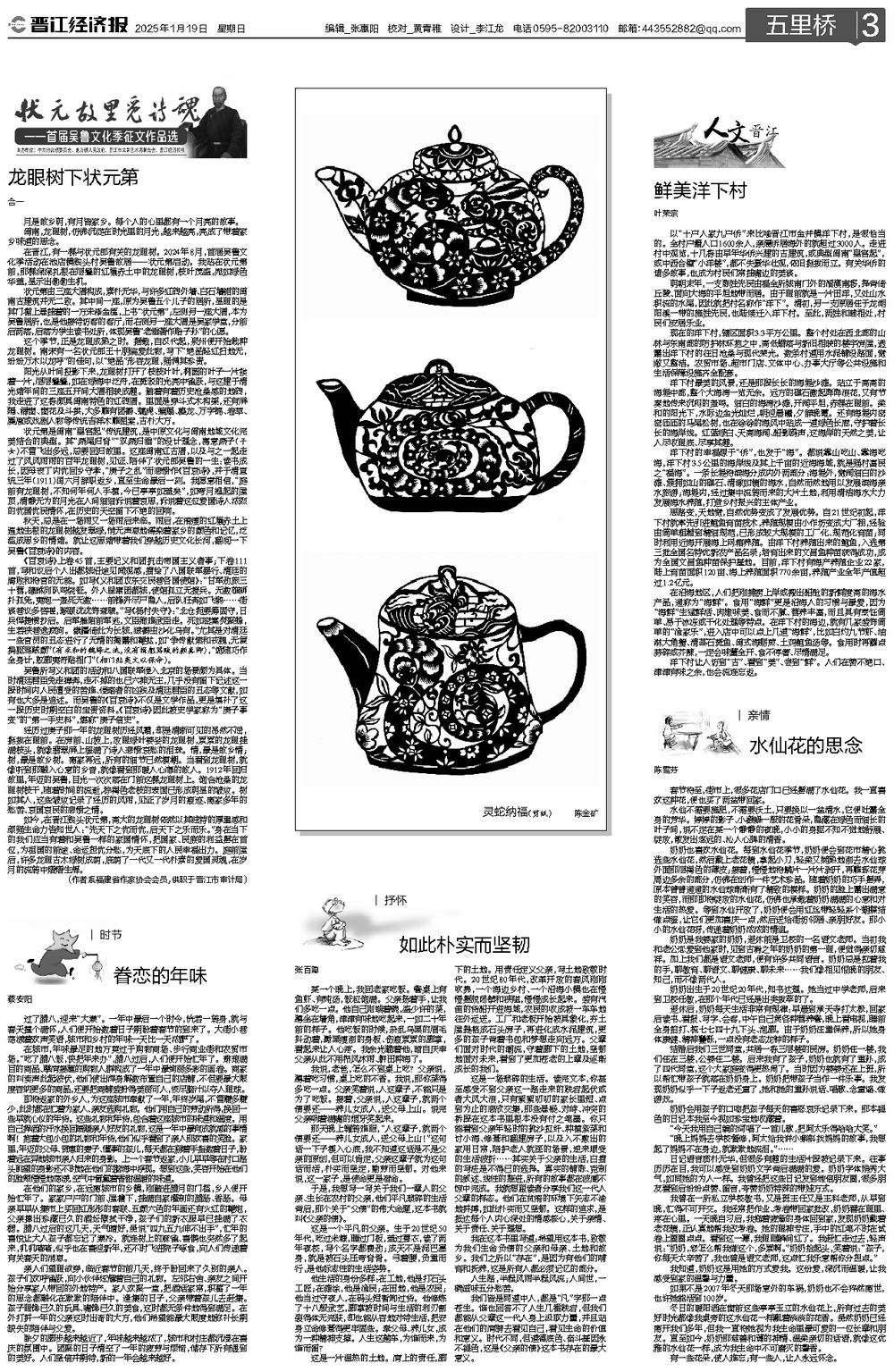张百隐
某一个晚上,我回老家吃饭。餐桌上有鱼虾、有炖汤,饭粒饱满。父亲扬着手,让我们多吃一点。他自己则端着碗,盛少许的菜,蹲坐在墙角,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一如二十年前的样子。他吃饭的时候,杂乱乌黑的眉毛抖动着,黝黑瘦削的身板、伤痕累累的脚掌,看起来让人心疼。我余光瞄着他,暗自庆幸父亲从此不用栉风沐雨、耕田种海了。
我说,老爸,怎么不到桌上吃?父亲说,蹲着吃习惯,桌上吃的不香。我说,那你菜得多吃一点。父亲笑着说,人这辈子,不能只是为了吃饭。接着,父亲说,人这辈子,就两个债要还——养儿女成人,送父母上山。说完父亲咧着满嘴的烟牙笑起来。
那天晚上辗转难眠,“人这辈子,就两个债要还——养儿女成人,送父母上山!”这句话一下子楔入心底,我不知道这话是不是父亲的原创,但可以肯定,父亲这辈子就为这句话而活,朴实而坚定,勤劳而坚韧。对他来说,这一家子,是使命更是宿命。
于是,我想写一写关于我们一辈人的父亲、生长在农村的父亲,他们平凡琐碎的生活背后,那个关于“父债”的伟大命题,这本书就叫《父亲的债》。
这是一个平凡的父亲。生于20世纪50年代,吃过米糠,睡过门板,盖过蓑衣,读了两年夜校,写个名字都费劲;成天不是泥巴裹身,就是被石头压弯脊骨。弓着腰,负重而行,是他标志性的生活姿势。
他生活的身份多样:在工地,他是打石头工匠;在滩涂,他是渔民;在田地,他是农民;他当过守夜人,在码头短暂卸过货。他修炼了十八般武艺,脚掌被时间与生活的利刃割裂得体无完肤,却也能从容地对待生活,把安身立命修葺得更牢固些。奉父母、养儿女,成为一种精神支撑。人生这趟车,为谁而来,为谁而留?
这是一片温热的土地。肩上的责任,脚下的土地。用责任定义父亲,写土地致敬时代。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拂,一个海边乡村、一个沿海小镇也在慢慢摆脱闭锁和狭隘,慢慢成长起来。装有汽笛的货船开进海域,农民的收成被一车车地往外运送。工厂和老板开始被具象化,夯土屋提格成石头房子,再进化成水泥建筑,更多的孩子背着书包和梦想走向远方。父辈们面对时代的潮流,守着脚下的土地,坚韧地面对未来,看到了更加苍老的上辈及逐渐成长的我们。
这是一场琐碎的生活。读完文本,你甚至感受不到父亲这一路走来的跌宕起伏或者大风大浪,只有絮絮叨叨的家长里短、点到为止的悲欣交集,那些悬疑、对峙、冲突的桥段在这本书里根本没有付之笔墨。你只能看到父亲年轻时的挑沙拉纤、种植紫菜和讨小海、修葺和翻建房子,以及入不敷出的家用日常,陪护老人就医的场景,逆来顺受的生活波折……其实关于父亲的生活,白描的写法是不得已的选择。真实的铺陈、克制的叙述、线性的推进,所有的故事都在波澜不惊中完成。我就想跟读者分享我们这一代人父辈的样态。他们在贫瘠的环境下矢志不渝地拼搏,如此朴实而又坚韧。这样的追求,是抵达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核心,关于亲情、关于责任、关于理想。
我在这本书里写道:希望用这本书,致敬为我们生命负债的父亲和母亲、土地和故乡。我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他们的哺育和抚养,这是所有人都必须记忆的部分。
人生路,半程风雨半程风流;人间世,一碗滋味五分愁苦。
我们皆是同道中人,都是“凡”字那一点苍生。谁也回答不了人生几番跌宕,但我们都能从父辈这一代人身上汲取力量,并且站在他们的肩膀去看见自己,看见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时代不同,但道德底色、奋斗基因永不褪色,这是《父亲的债》这本书存在的最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