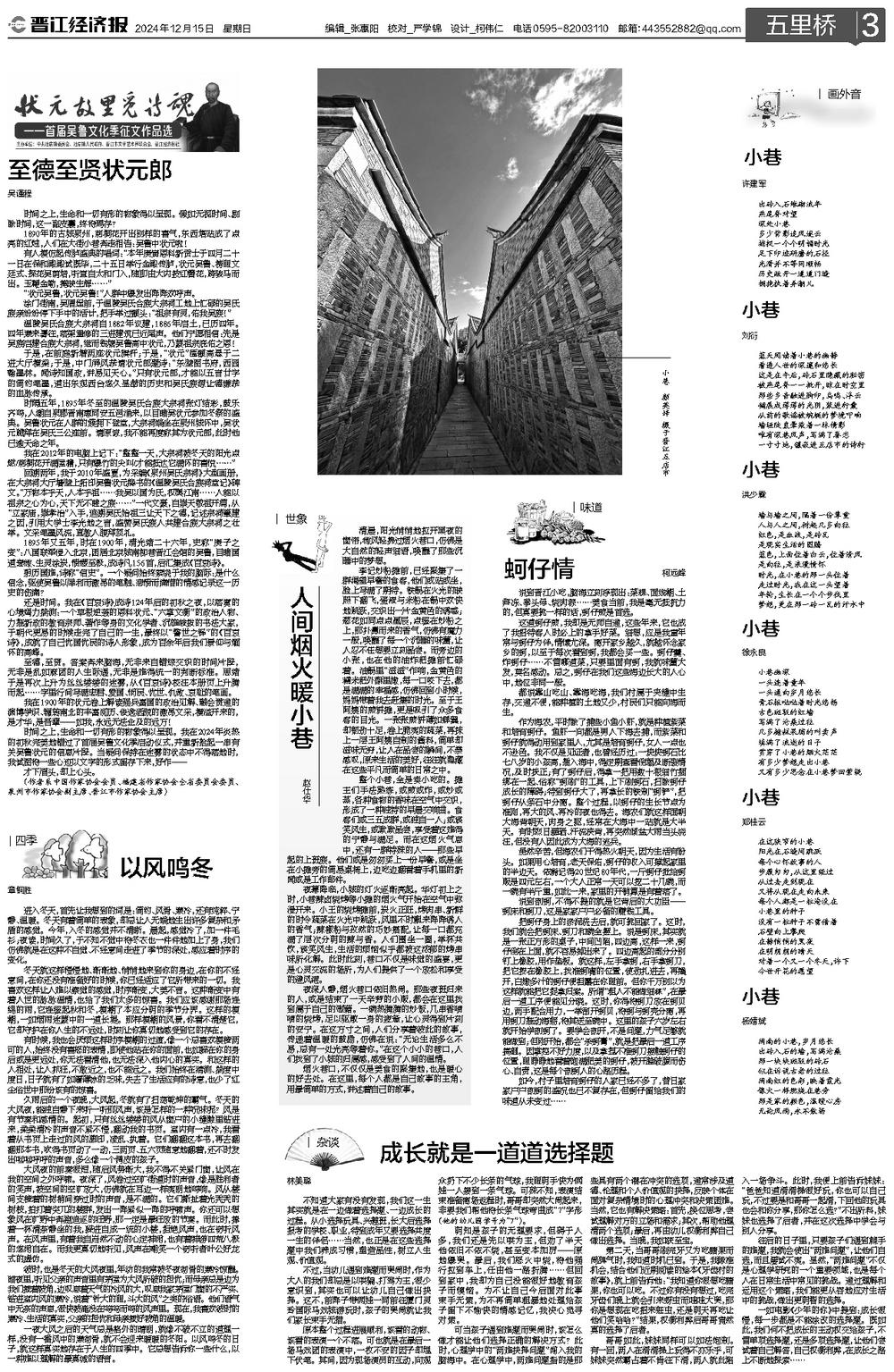柯远峰
说到晋江小吃,脑海立刻浮现出:菜粿、面线糊、土笋冻、拳头母、烧肉粽……美食当前,我是毫无抵抗力的,但真要挑一样的话,蚵仔煎是首选。
这道蚵仔煎,我却是无师自通,这些年来,它也成了我招待客人时必上的拿手好菜。细想,应是我童年常与蚵仔为伴,情愫尤深。离开家乡越久,就越怀念家乡的蚵,以至于每次看到蚵,我都会买一些。蚵仔羹、炸蚵仔……不管哪道菜,只要里面有蚵,我就味蕾大发,莫名感动。总之,蚵仔在我们这些海边长大的人心中,地位非同一般。
都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我们村属于夹缝中生存,交通不便,能种植的土地又少,村民们只能向海而生。
作为海农,平时除了捕些小鱼小虾,就是种植紫菜和培育蚵仔。鱼虾一向都是男人下海去捕,而紫菜和蚵仔就得动用到家里人,尤其是培育蚵仔,女人一点也不逊色。我不仅是见证者,也曾经历过:一块块蚵石比七八岁的小孩高,插入海中,得定期查看倒塌及断裂情况,及时扶正;有了蚵仔后,得拿一把用数十根细竹捆绑在一起、俗称“蚵刷”的工具,上下刷蚵石,扫除蚵仔成长的障碍;待到蚵仔大了,再拿长的铁制“蚵铲”,把蚵仔从条石中分离。整个过程,以蚵仔的生长节点为准则,再大的风、再冷的夜也得去。海农们就这样面朝大海背朝天,肉身之躯,经常在大海中一站就是大半天。有时烈日暴晒、汗流浃背,再突然倾盆大雨当头浇注,但没有人因此成为大海的逃兵。
虽然辛苦,但海农们干得热火朝天,因为生活有盼头。如果用心培育,老天保佑,蚵仔的收入可撑起家里的半边天。依稀记得20世纪80年代,一斤蚵仔批给蚵贩是四元左右,一个大人正常一天可以挖二十几碗,而一碗有半斤重,如此一来,家里的开销算是有着落了。
说到剖蚵,不得不提的就是它背后的大功臣——蚵床和蚵刀,这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赚钱工具。
把蚵仔身上的淤泥洗去后,就可挑回家了。这时,我们就会把蚵床、蚵刀和碗全摆上。说是蚵床,其实就是一张正方形的桌子,中间凹陷,四边高,这样一来,蚵仔倒在上面,就不容易掉出来了。四边高起的部分分别钉上橡胶,用作垫板。就这样,左手拿蚵,右手拿蚵刀,把它按在橡胶上,找准蚵嘴的位置,使劲扎进去,再撬开,白嫩多汁的蚵仔便袒露在你眼前。但你千万别以为这样就能把它捉拿归案。所谓“粗人不能做细粿”,在最后一道工序便能见分晓。这时,你得将蚵刀放在蚵贝边,两手配合用力,一举刮开蚵贝,将蚵与蚵壳分离,再用蚵刀推动海蛎,将其送至碗中。这里的孩子六岁左右就开始学剖蚵了。要学会剖开,不是问题,力气足够就能做到;但刚开始,都会“杀蚵膏”,就是把最后一道工序搞砸。因掌控不好力度,以及拿捏不准蚵刀接触蚵仔的位置,眼睁睁地看着饱满肥美的蚵仔,被开膛破腹而伤心、自责,这是每个剖蚵人的心路历程。
如今,村子里培育蚵仔的人家已经不多了,昔日家家户户剖蚵的盛况也已不复存在,但蚵仔留给我们的味道从未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