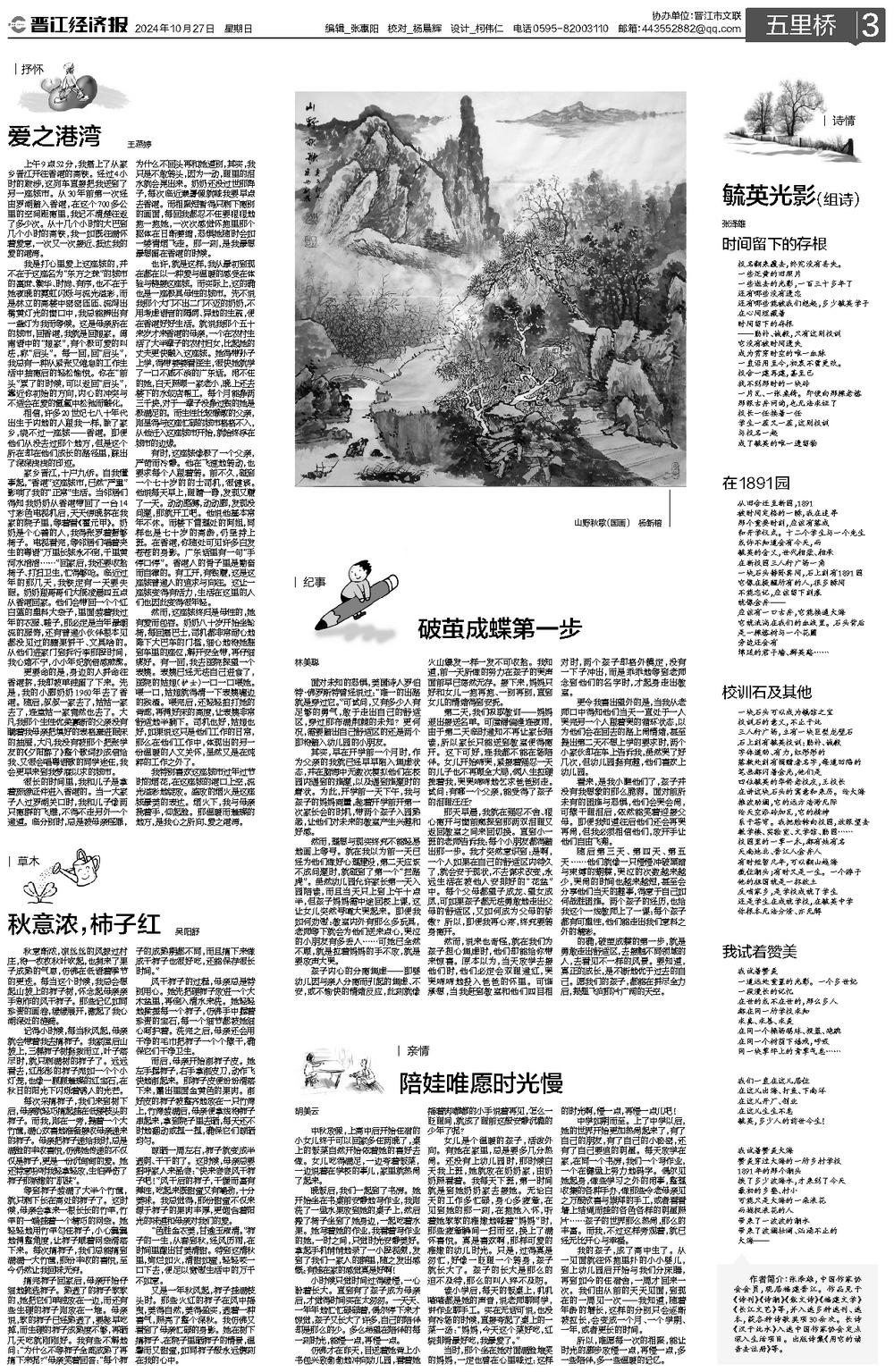王燕婷
上午9点52分,我搭上了从家乡晋江开往香港的高铁。经过4小时的跋涉,这列车直接把我送到了另一座城市。从30年前第一次经由罗湖踏入香港,在这个700多公里的空间距离里,我记不清楚往返了多少次。从十几个小时的大巴到几个小时的高铁,我一如既往满怀着爱意,一次又一次接近、抵达我的爱的港湾。
我是打心里爱上这座城的,并不在于这座名为“东方之珠”的城市的富庶、繁华、时尚、有序,也不在于她夜晚的霓虹闪烁与流光溢彩,而是林立的高楼中密密匝匝、流泻出橘黄灯光的窗口中,我总能辨出有一盏灯为我而等候。这是母亲所在的城市,回香港,我就是回娘家。闽南语中的“娘家”,有个极可爱的叫法,称“后头”。每一回,回“后头”,我总有一种从紧张又倦怠的工作生活中抽离后的轻松愉悦。你在“前头”累了的时候,可以返回“后头”,靠近你初始的方向,内心的冲突与不适会在爱的氤氲中松弛而融化。
相信,许多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于内地的人跟我一样,除了家乡,绕不过一座城——香港。即便他们从没去过那个地方,但是这个所在却在他们成长的路径里,踩出了深深浅浅的印迹。
家乡晋江,十户九侨。自我懂事起,“香港”这座城市,已然“严重”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当邻居们得知我奶奶从香港带回了一台14寸彩色电视机后,天天傍晚挤在我家的院子里,等着看《霍元甲》。奶奶是个心善的人,我得张罗着摆够椅子。电视看完,等邻居们唱着夹生的粤语“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回家后,我还要收拾椅子、打扫卫生,忙得够呛。临近过年的那几天,我铁定有一天要失眠。奶奶跟哥哥们大概凌晨四五点从香港回家。他们会带回一个个红白蓝的塑料大袋子,里面装着我过年的衣服、鞋子,那必定是当年最潮流的服饰,还有普通小伙伴根本见都没见过的糖果饼干、文具啥的。从他们进家门到拆行李那段时间,我心绪不宁,小小年纪就倍感煎熬。
更要命的是,身边的人拼命往香港挤,我却被单独留了下来。先是,我的小脚奶奶1960年去了香港。随后,叔叔一家去了,姑姑一家去了,连堂姑一家竟然也去了。大凡我那个生性优柔寡断的父亲没有瞒着我母亲把填好的表格塞进眠床的抽屉,大凡我没有被那个把张学友的《夕阳醉了》整个歌词抄成信给我、又很会唱粤语歌的同学迷住,我会更早来到我梦寐以求的城市。
很长的时间里,我和儿子是拿着旅游证件进入香港的。当一大家子人过罗湖关口时,我和儿子像两只离群的飞雁,不得不走另外一个通道。临分别时,总是被母亲怪罪,为什么不回头再和她道别,其实,我只是不敢转头,因为一动,眼里的泪水就会晃出来。奶奶还没过世那阵子,每次临近寒暑假就喊我要早点去香港。而相聚短暂得只剩下离别的画面,每回我都忍不住要狠狠地抱一抱她,一次次感觉怀抱里那个躯体在日渐萎缩,恐惧她随时会如一缕青烟飞走。那一刻,是我最想最想留在香港的时候。
也许,就是这样,我从最初到现在都在以一种爱与温暖的感受在体验与链接这座城。而实际上,这的确也是一座极具母性的城市。先不说我那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奶奶,不用考虑语言的隔阂、异地的生疏,便在香港好好生活。就说我那个五十来岁才来香港的母亲,一个在农村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农村妇女,比起她的丈夫更快融入这座城。她得带孙子上学,得带婆婆看医生,很快她就学了一口不咸不淡的广东话。闲不住的她,白天照顾一家老小,晚上还去楼下的水饺店帮工。每个月能挣两三千块,对于一辈子没挣过钱的她是极满足的。而生性比较懒散的父亲,则显得与这座忙碌的城市格格不入,从他迁入这座城市开始,就始终浮在城市的边缘。
有时,这座城像极了一个父亲,严苛而冷静。他在飞速地转动,也要求每个人跟着转。前不久,碰到一个七十岁的的士司机,很健谈。他说每天早上,眼睛一睁,发现又赚了一天。动动胳膊,动动脚,发现没问题,那就开工吧。他说他基本常年不休。而楼下管理处的阿姐,同样也是七十岁的高龄,仍坚持上班。在香港,你随处可见许多白发苍苍的身影。广东话里有一句“手停口停”。香港人的骨子里是勤奋而自律的。有工开,有钱赚,这是这座城普通人的追求与向往。这让一座城变得有活力,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因此变得很年轻。
然而,这座城终归是母性的,她有爱而包容。奶奶八十岁开始坐轮椅,每回搭巴士,司机都非常耐心地降下大巴车的门槛,细心地将她推到车里的座位,解开安全带,再仔细绑好。有一回,我去医院探望一个表姨。表姨已经无法自己进食了,医院的姑娘(护士)一口一口喂她。喂一口,姑娘就得清一下表姨嘴边的残渣。喂完后,还轻轻拍打她的背部,再调好床的高度,让表姨非常舒适地半躺下。司机也好,姑娘也好,如果说这只是他们工作的日常,那么在他们工作中,体现出的另一份温暖的人文关怀,显然又是在纯粹的工作之外了。
我特别喜欢这座城市过年过节时的烟花,在这座城的港口上空,流光溢彩地绽放。盛放的烟火是这座城最美的表达。烟火下,我与母亲挽着手,仰起脸。那温暖而璀璨的地方,是我心之所向、爱之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