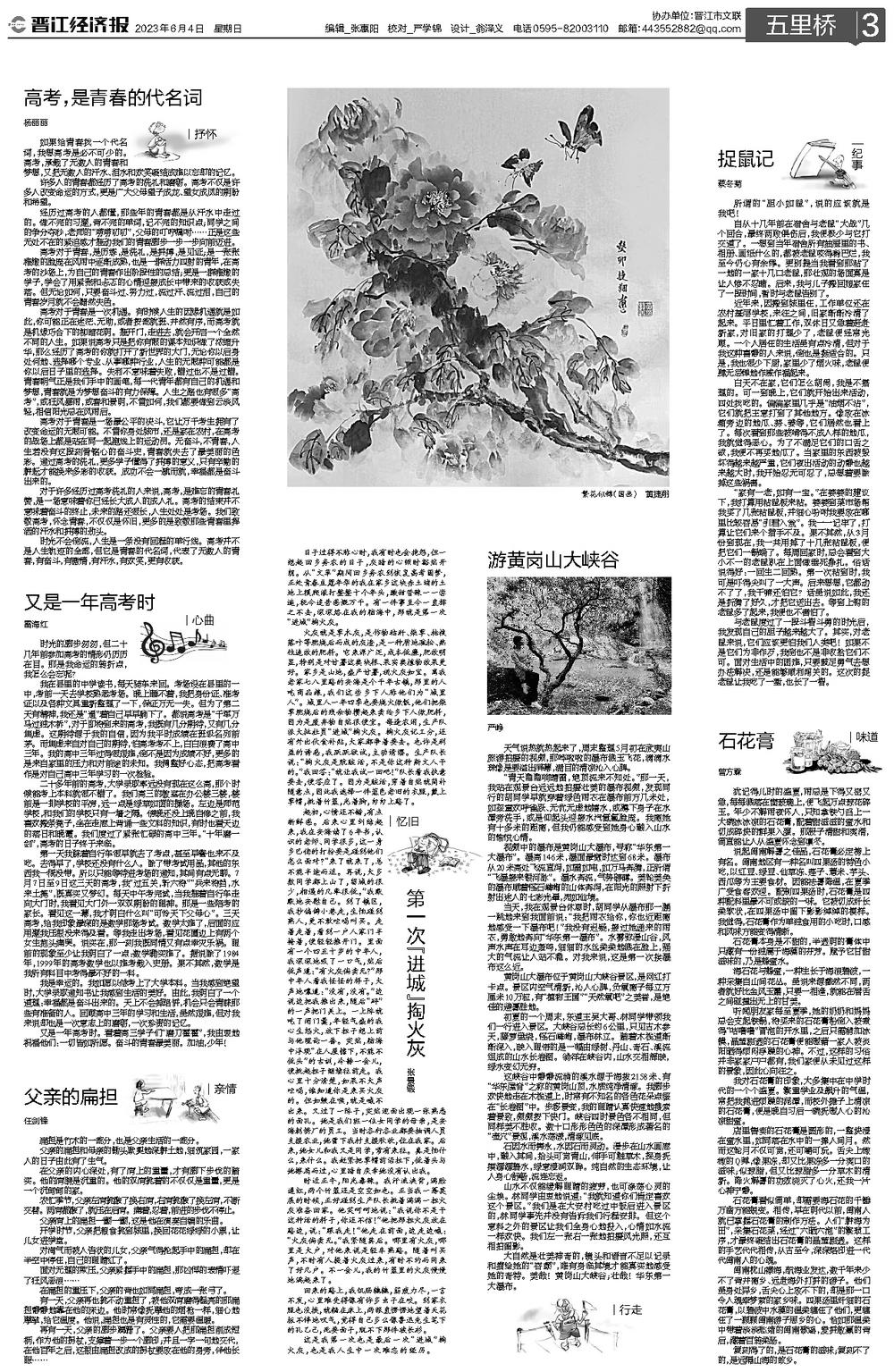日子过得不称心时,我有时也会抱怨,但一想起回乡务农的日子,灰暗的心顿时豁然开朗。从“文革”期间回乡务农到恢复高考圆梦,正处青春豆蔻年华的我在家乡这块赤土埔的土地上摸爬滚打整整十个年头,酸甜苦辣一一尝遍,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有一件事至今一直挥之不去,深深烙在我的脑海中,那就是第一次“进城”掏火灰。
火灰就是草木灰,是作物秸秆、柴草、枯枝落叶等燃烧后而成的灰渣,是一种质地疏松、热性速效的肥料。它来源广泛,成本低廉,肥效明显,特别是对甘薯这类块根、果实类植物效果更好。家乡是山地,盛产甘薯,视火灰如宝。离我老家七八里路的安海是个千年古镇,那里的人吃商品粮,我们这些乡下人称他们为“城里人”。城里人一年四季也要烧火做饭,他们把柴草燃烧后的残余物攒起来卖给乡下人做肥料,因为是废弃物自然很便宜。每逢农闲,生产队派大批社员“进城”掏火灰。掏火灰记工分,还有外出伙食补贴,大家都争着要去。也许是利益的诱惑,我跃跃欲试,主动请缨。生产队长说:“掏火灰是肮脏活,不是你这种斯文人干的。”我回答:“就让我试一回吧!”队长看我执意要去,便答应了。因为是脏活,穿着自然就简朴随意点,因此我选择一件蓝色老旧的衣服,戴上草帽,挑着竹篮,光着脚,匆匆上路了。
起初,心情还不错,有点新鲜感。后来心里纠结起来,我在安海读了6年书,认识的老师、同学很多,这一身乡巴佬的打扮要是碰到他们怎么面对?“来了就来了,总不能半途而返。再说,大多数同学都上山了,留城的很少,相遇的几率很低。”我默默地安慰自己。到了镇区,我抄偏僻小巷走,生怕碰到熟人,更不敢吆喝叫买。走着走着,看到一户人家门半掩着,便轻轻推开门。里面有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低声道:“有火灰倘卖无?”那中年人看我怪怪的样子,大声地嚷道:“没有,没有。”边说边把我推出来,随后“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一上阵就吃了闭门羹,年轻气盛的我心生怒火,放下担子想上前与他理论一番。突然,脑海中浮现“在人屋檐下,不能不低头”的古训,冷静一会儿,便挑起担子继续往前走。我心里十分清楚,如果不大声吆喝,谁知道你是来买火灰的。但如鲠在喉,就是喊不出来。又过了一阵子,突然迎面出现一张熟悉的面孔。她是我们班一位女同学的母亲,是安海刺绣厂的员工。当时各行各业都要抽调人员支援农业,她曾下我村支援秋收,住在我家。后来,她女儿和我又是同学,常有来往。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我赶紧把草帽前沿拉下,低着头与她擦肩而过,心里暗自庆幸她没有认出我。
时近正午,阳光毒辣。我汗流浃背,满脸通红,两个竹篮还是空空如也。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正好碰到生产队长挑着满满一担火灰准备回家。他笑呵呵地说:“我说你不是干这种活的料子,你还不信!”他把那担火灰放在路边,说:“跟我走!”他走在前面,边走边喊:“火灰倘卖无。”我紧随其后。哪里有火灰,哪里是大户,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随着叫买声,不时有人提着火灰过来,有时不约而同来了好几户。不一会儿,我的竹篮里的火灰慢慢地满起来了。
回来的路上,我饥肠辘辘,筋疲力尽,一言不发,心里难受得像有许多虫子在咬。到家衣服也没换,就躺在床上,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不停地叹气,觉得自己多么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死要面子,脱不下那件破长衫。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城”掏火灰,也是我人生中一次难忘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