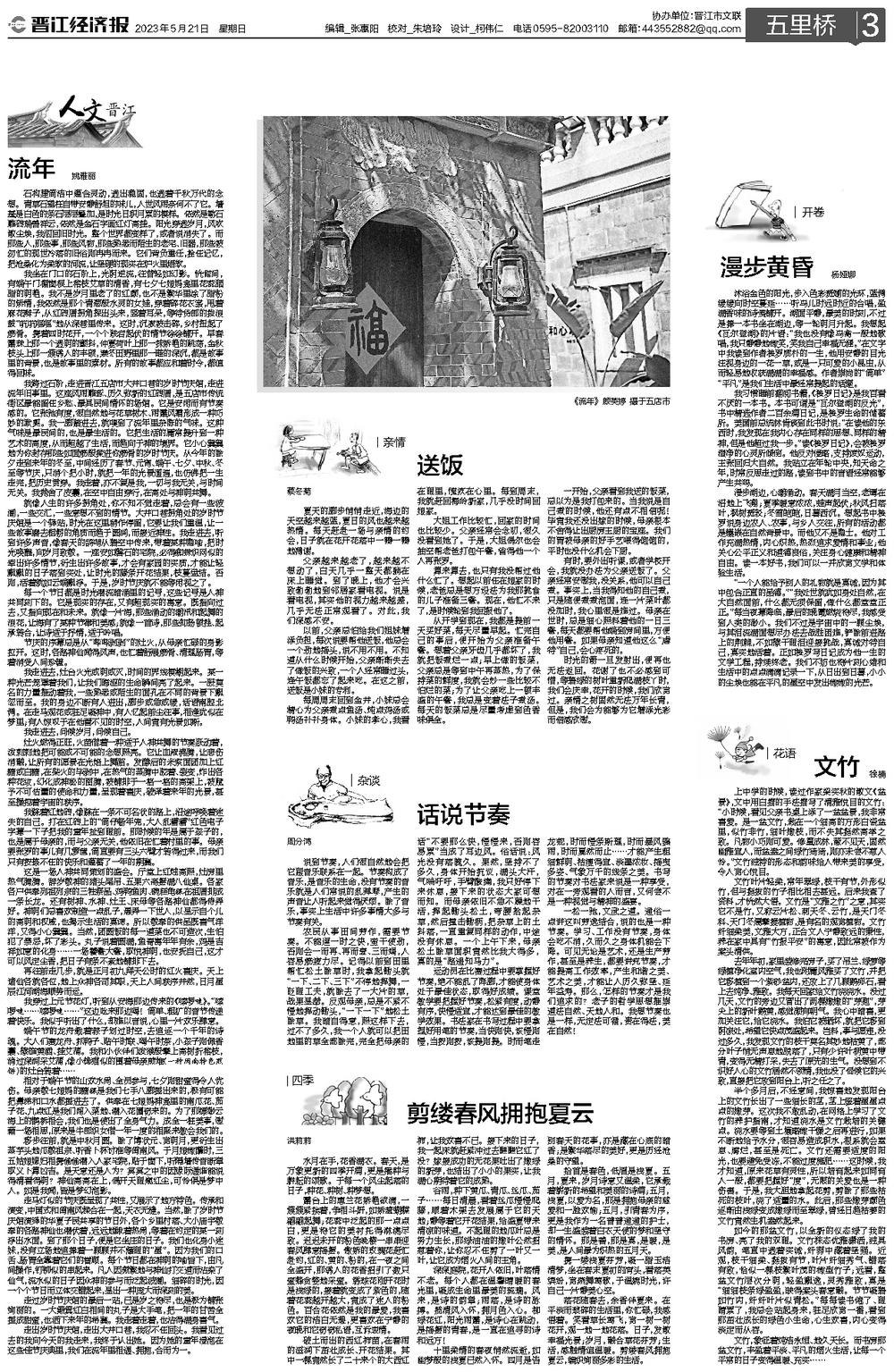姚雅丽
石构建简洁中蕴含灵动,透出稳固,也透着千秋万代的念想。青草石望柱自带安静舒坦的味儿,人世风雨奈何不了它。墙基是白色的条石层层叠加,是时光日积月累的模样。依然是勒石雕砖瑞兽祥云,依然是金石字画红灯高挂。阳光穿透岁月,风吹散尘埃,我泅回旧时光。整个世界都变样了,或者说消失了。而那些人,那些事,那些风物,那些熟悉而陌生的老宅、旧器,那些被匆忙的现世冷落的旧俗则冉冉而来。它们背负重任,拴住记忆,把沧桑化为柔软的河流,让坚硬的现实在炉火里焐软。
我坐在门口的石阶上,光阴逆流,往昔轻如幻影。恍惚间,有端午门楣窗棂上榕枝艾草的清香,有七夕七娘妈龛里花蕊胭脂的明艳。我不是岁月里老了的红颜,也不是繁华里涂了脂粉的矫情,我依然是那个青葱般水灵的女娃,穿着碎花衣裳,甩着麻花辫子,从红砖厝拐角探出头来,竖着耳朵,等待货郎的拨浪鼓“吭吭哐哐”地从深巷里传来。这时,沉寂被击碎,乡村扭起了筋骨。携着四时花开,一个个跌宕起伏的情节徐徐铺开。早春露珠上那一个透明的颤抖,仲夏荷叶上那一抹娇艳的跳荡,金秋枝头上那一簇诱人的丰硕,寒冬田野里那一畦的深沉,都是故事里的背景,也是故事里的素材。所有的故事都应和着时令,都值得回味。
我跨过石阶,走进晋江五店市大井口巷的岁时节庆馆,走进流年旧事里。这座风雨雕琢、历久弥新的红砖厝,是五店市传统街区最能留住乡愁、最具民间情怀的场馆。它是安闲而有节奏感的。它张弛有度,很自然地与花草树木、雨露风霜形成一种巧妙的默契。我一脚踏进去,就嗅到了流年里杂陈的气味。这种气味是最民间的,也是最生活的。它把生活的庸常提升到一种艺术的高度,从而超越了生活,而趋向于神的境界。它小心翼翼地为你封存那些如面筋般揉进你筋骨的岁时节庆。从今年的除夕走到来年的冬至,中间经历了春节、元宵、端午、七夕、中秋、冬至等节庆,只消个把小时,就把一年的光景遛遍,也仿佛把一生走完,把历史贯穿。我走着,亦不复是我,一切与我无关,与时间无关。我抛舍了皮囊,在空中自由穿行,在高处与神明共舞。
就像人生的许多拐角处,你不知不觉走着,总会有一些波澜,一些交汇,一些意想不到的情节。大井口巷拐角处的岁时节庆馆是一个驿站,时光在这里稍作停留,它要让我们重温,让一些故事磨去粗粝的角质而趋于圆润,而接近神性。我走进去,听到许多声音,像春天的鸽哨从碧空中传来,带着某种隐喻,把时光唤醒,向岁月致敬。一座安如磐石的宅院,必得蜘蛛织网似的牵出许多情节,衍生出许多故事,才会有家园的实质,才能让轻飘飘的日子落到实处,让时光的藤条开花结果,枝蔓盘结。否则,活着就如云端飘浮。于是,岁时节庆就不能等闲视之了。
每一个节日都是时光潜流暗涌里的记号,这些记号是人神共同刻下的。它是现实的存在,又有超现实的寓意。既指向过去,又指向现在和未来。就像一片海,那些涌动的潮汛和起舞的浪花,让海有了某种节律和美感;就像一首诗,那些抑扬顿挫、起承转合,让诗适于抒情,适于吟唱。
节庆的序幕总是从“哔哔剥剥”的灶火,从母亲忙碌的身影拉开。这时,各路神仙闻得风声,也忙着舒展筋骨、清理肠胃,等着消受人间珍馐。
我走进去,灶台火光或明或灭,时间的界线模糊起来。某一种光芒笼罩着我们,让我们晦涩的生命瞬间亮了起来。一股莫名的力量推动着我,一些熟悉或陌生的面孔在不同的背景下飘忽而至。我的身边不断有人进出,脚步或急或缓,话语南腔北调。在走马观花或驻足凝神中,有人忆起前尘往事,相逢犹似在梦里;有人惊叹于在他看不见的时空,人间竟有光景如斯。
我走进去,问候岁月,问候自己。
灶火燃得正旺,火苗借着一种适于人神共舞的节奏跃动着,泼剌剌地把可能或不可能的念想照亮。它让血液沸腾,让悲伤消融,让所有的愿景在光焰上舞蹈。发酵后的米浆面团加上红糖或白糖,在柴火的毕剥中,在热气的蒸腾中胶着、裂变,炸出各种花纹,幻化成神秘的图腾,被铺排于一格一格的高架上,被赋予不可估量的使命和力量,呈现着喜庆,破译着来年的光景,甚至操控着宇宙的秩序。
我踩着红地砖,像踩在一条不可名状的路上,沿途呼唤着迷失的自己。打在红砖上的“简仔畅年兜,大人乱糟糟”红色电子字幕一下子把我的童年扯到眼前。那时候的年是属于孩子的,也是属于母亲的,而与父亲无关,他依旧在忙着村里的事。母亲要张罗的事儿有几箩筐,简直要有三头六臂才转得过来,而我们只有按捺不住的快乐和蕴蓄了一年的期冀。
这是一场人神共同策划的盛会。厅堂上红烛高照,灶房里热气腾腾。辞岁敬神的猪头尾吊、五果六斋摆满八仙桌。各家各户供奉列祖列宗的三牲祭品、鸡鸭鱼肉、碗糕龟粿在祖厝排成一条长龙。还有树神、水神、灶王、床母等各路神仙都得侍弄好。神明们总喜欢制造一点乱子,愚弄一下世人,以显示自个儿的高明和权威,也揭示生活的真谛。所以敬奉的供品既喜气洋洋,又得小心翼翼。当然,团圆饭的每一道菜也不可造次,生怕犯了禁忌,坏了彩头。丸子说着圆满,鱼寄寓年年有余,鸡是吉祥如意的化身……一场饕餮大餐,取悦神明,也安抚自己,这才可以风定尘香,把日子有条不紊地铺排下去。
再往前走几步,就是正月初九拜天公时的红火喜庆。天上诸仙各就各位,地上众神各司其职,天上人间秩序井然,日月星辰江河湖海顺势而运。
我穿过上元节花灯,听到从安海那边传来的《嗦啰嗹》。“嗦啰嗹……嗦啰嗹……”这边吆来那边喝!简单、粗犷的音节传递着快乐。我似乎听出了什么,却难以言说,心里一片欢乐肆意。
端午节的龙舟载着粽子划过时空,去追逐一个千年的诗魂。大人们赛龙舟、抓鸭子、贴午时联、喝午时茶,小孩子则佩香囊、擦雄黄酒、挂艾蒲。我和小伙伴们泼猴般攀上高树折榕枝,淌过深涧采艾蒲,像小馋猫似的围着母亲煎堆(一种闽南特色煎饼)的灶台转着……
相对于端午节的山欢水闹、全员参与,七夕则甜蜜得令人忧伤。母亲敬七娘妈的糖粿是我们七手八脚搓出来的,极有可能把鼻涕和口水都搓进去了。供奉在七娘妈神龛里的南瓜花、茄子花、九点红是我们闯入菜地、潜入花圃窃来的。为了那缥缈云海上的鹊桥相会,我们也是使出了全身气力。成全一桩美事,慰藉一场相思,原来是牛郎织女借一年一度的相聚来教会我们的。
移步往前,就是中秋月圆。除了博状元、赏明月,更衍生出蒸芋头地瓜敬祖宗、听香卜杯讨准等闽南风。于月娘微醺时,三五姑娘媳妇相携偷偷潜入人家宅院,贴于窗下,听隔墙传音断章取义卜算凶吉。是天意还是人为?冥冥之中的因缘际遇谁能说得清看得明?神仙高高在上,偶开天眼窥红尘,可怜俱是梦中人。如是我闻,皆是梦幻泡影。
走马灯似的节庆既呈现了共性,又展示了地方特色。传承和演变,中国式和闽南风糅合在一起,天衣无缝。当然,除了岁时节庆馆演绎的华夏子民共享的节日外,各个乡里村落、大小庙宇敬奉的各路神仙也潜伏着,远远地瞅着热闹,等着在约定的某一刻浮出水面。到了那个日子,便是它坐庄的日子。我们也化身小迷妹,没有立场地追捧着一颗颗并不耀眼的“星”。因为我们的口舌、肠胃全靠着它们的眷顾。每个节日都在神明的喻旨下,由凡间操作,钉铆似的串起来。凡人因频繁地与神仙打交道而沾染了仙气,流水似的日子因众神的参与而泛起波澜。细碎的时光,因一个个节日而立体交错起来,显出一种庞大而深刻的美。
走过岁时节庆馆的最后一站,已是岁之将尽,也是极为铺张绚丽的。一大簸箕红白相间的丸子是大手笔,把一年的甘苦全搓成甜蜜,也洒下来年的希冀。我走着走着,也沾得满身喜气。
走出岁时节庆馆,走出大井口巷,我忍不住回头。我看见过去的我向今天的我走来,我终于认出她。因为她的童年浸泡在这些佳节庆典里,我们在流年里相遇、拥抱,合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