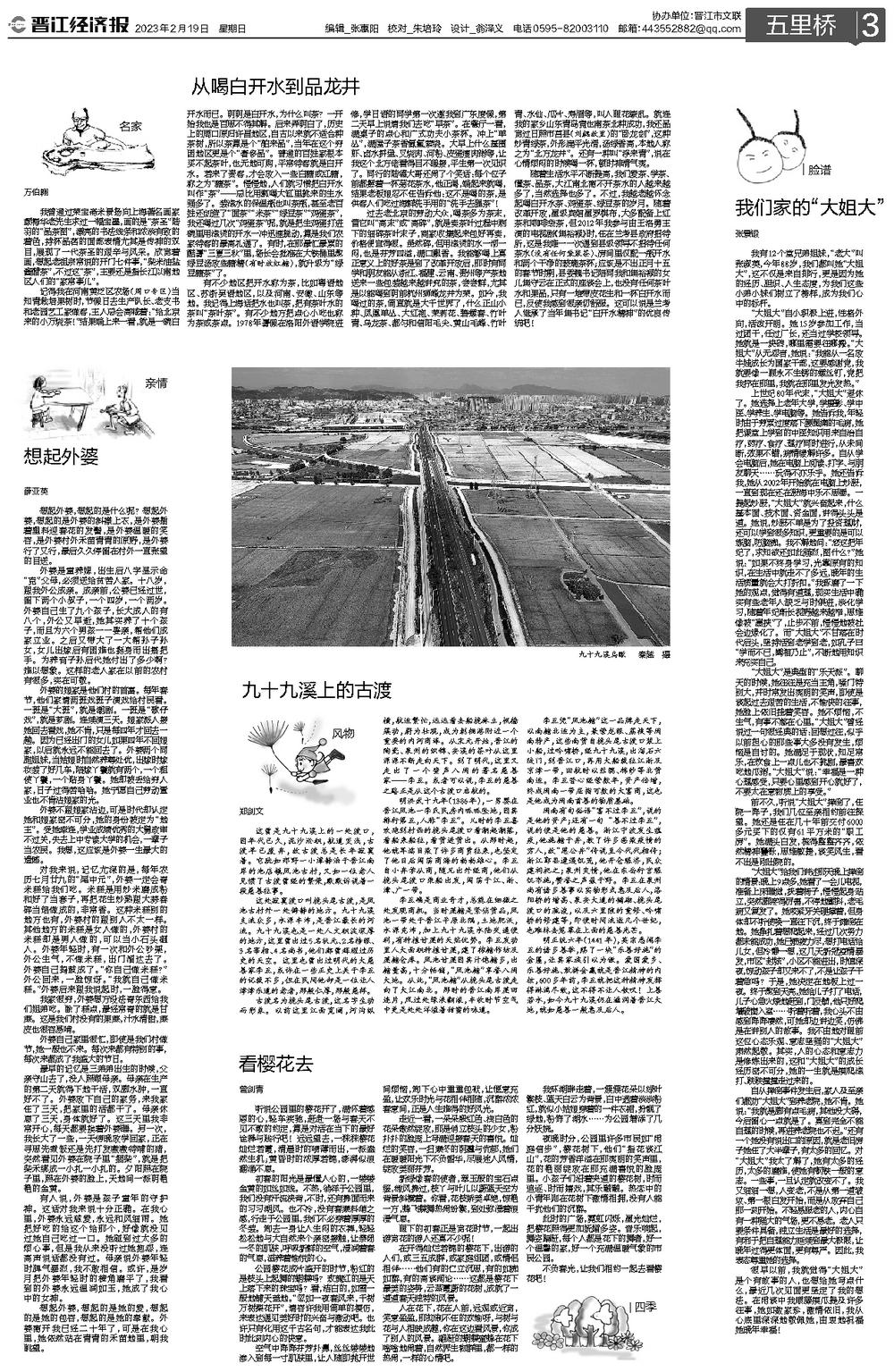薛亚英
想起外婆,想起的是什么呢?想起外婆,想起的是外婆的斜襟上衣,是外婆插着塑料迎春花的发髻,是外婆温暖的笑容,是外婆村外禾苗青青的原野,是外婆行了又行,最后久久停留在村外一直张望的目送。
外婆是童养媳,出生后八字显示命“克”父母,必须送给贫苦人家。十八岁,跟我外公成亲。成亲前,公婆已经过世,留下两个小叔子,一个四岁,一个两岁。外婆自己生了九个孩子,长大成人的有八个,外公又早逝,她其实养了十个孩子,而且为六个男孩一一娶亲,帮他们成家立业。之后又带大了一大帮孙子孙女,女儿出嫁后有困难也挺身而出搭把手。为养育子孙后代她付出了多少啊?难以想象。这样的老人家在以前的农村有很多,实在可敬。
外婆的娘家是他们村的首富。每年春节,他们家请两班戏班子演戏给村民看。一班是“大班”,就是潮剧。一班是“歌仔戏”,就是芗剧。连续演三天。娘家派人接她回去看戏,她不肯,只是每四年才回去一趟。因为已经出门的女儿如果四年不回娘家,以后就永远不能回去了。外婆两个同胞姐妹,当姑娘时自然养尊处优,出嫁时嫁妆装了好几车,陪嫁丫鬟就有两个,一个粗使丫鬟,一个贴身丫鬟。她却被丢给穷人家,日子过得苦哈哈。她宁愿自己劳动置业也不肯沾娘家的光。
外婆不跟娘家沾边,可是时代却认定她和娘家密不可分,她的身份被定为“地主”。受她牵连,学业成绩优秀的大舅政审不过关,失去上中专读大学的机会,一辈子当农民。我想,这应该是外婆一生最大的遗憾。
对我来说,记忆尤深的是,每年农历七月廿九的“尾中元”,外婆一定会寄米糕给我们吃。米糕是用炒米磨成粉和好了当套子,再把花生炒熟跟大蒜舂碎当馅做成的,非常香。这种米糕别的地方也有,外婆村的跟别人不太一样。其他地方的米糕是女人做的,外婆村的米糕却是男人做的,可以当小石头砸人。外婆年轻时,有一次和外公吵架,外公生气,不做米糕,出门溜达去了。外婆自己捣鼓成了。“你自己做米糕?”外公回来,一脸惊讶。“我就自己做米糕。”外婆后来跟我说起时,一脸得意。
我家很穷,外婆想方设法寄东西给我们姐弟吃。除了糕点,最经常寄的就是甘蔗。这是我们村没有的果蔗,汁水清甜,蔗皮也很容易啃。
外婆自己家里很忙,即使是我们村做节,她一般也不来。每次来都有特别的事,每次来都成了我盛大的节日。
最早的记忆是三弟弟出生的时候,父亲守山去了,没人照顾母亲。母亲在生产的第二天就得下地干活,双脚水肿,一直好不了。外婆放下自己的家务,来我家住了三天,把家里的活都干了。母亲休息了三天,身体就好了。这三天里我非常开心,每天都要挨着外婆睡。另一次,我长大了一些,一天傍晚放学回家,正在寻思先煮饭还是先打发嗷嗷待哺的猪,突然看见外婆在院子里“捆柴”,就是把柴禾绑成一小扎一小扎的。夕阳照在院子里,照在外婆的脸上,天地间一派明艳艳的金黄。
有人说,外婆是孩子童年的守护神。这话对我来说十分正确。在我心里,外婆永远慈爱,永远和风细雨。她把好吃的给这个给那个,好像就没见过她自己吃过一口。她碰到过太多的烦心事,但是我从来没听过她抱怨,连高声说话都没有过。母亲说外婆年轻时脾气暴烈,我不敢相信。或许,是岁月把外婆年轻时的棱角磨平了,我看到的外婆永远温润如玉,她成了我心中的女神。
想起外婆,想起的是她的爱,想起的是她的包容,想起的是她的奉献。外婆离开我已经二十年了,可是在我心里,她依然站在青青的禾苗地里,朝我眺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