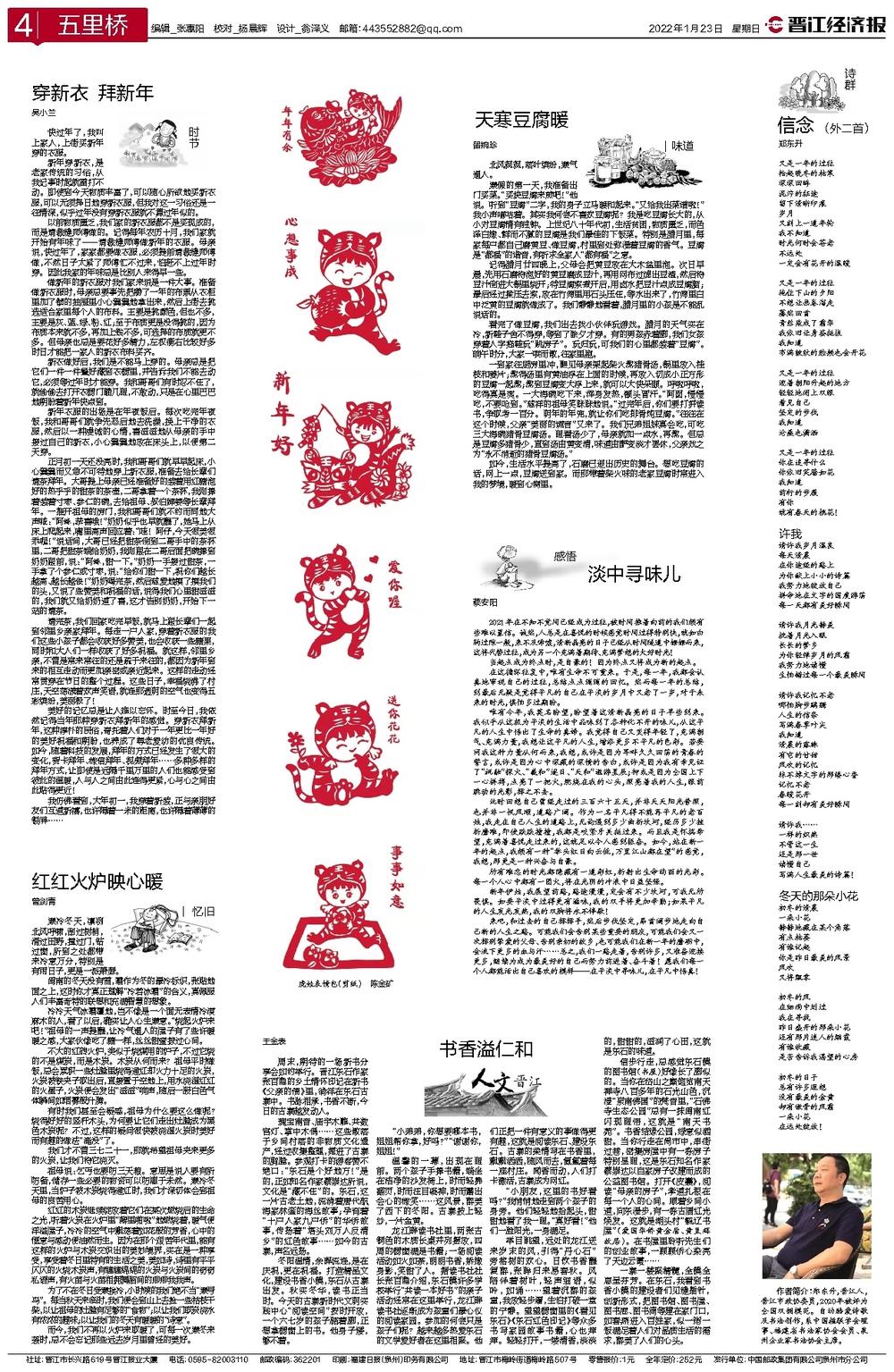留婉珍
北风飒飒,落叶缤纷,寒气逼人。
寒假的第一天,我准备出门买菜。“买块豆腐来煎吧!”他说。听到“豆腐”二字,我的身子立马暖和起来。“又给我出菜谱啦!”我小声嘀咕着。其实我何尝不喜欢豆腐呢?我是吃豆腐长大的,从小对豆腐情有独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生活贫困,物质匮乏,而色泽白嫩、鲜而不腻的豆腐是我们最佳的下饭菜。特别是腊月里,每家每户都自己磨黄豆、做豆腐,村里到处弥漫着豆腐的香气。豆腐是“都福”的谐音,有祈求全家人“都有福”之意。
记得腊月廿四晚上,父母会把黄豆放在大木盆里泡。次日早晨,先用石磨将泡好的黄豆磨成豆汁,再用网布过滤出豆渣,然后将豆汁倒进大锅里烧开;待豆腐浆煮开后,用卤水把豆汁点成豆腐脑;最后经过揉压去浆,放在竹筛里用石头压住,等水出来了,竹筛里白中泛黄的豆腐就做成了。我们静静地看着,腊月里的小孩是不能乱说话的。
看完了做豆腐,我们出去找小伙伴玩游戏。腊月的天气实在冷,新鞋子舍不得穿,等到了除夕才穿。有的男孩赤着脚,我们女孩穿着人字拖鞋玩“跳房子”。玩归玩,可我们的心里都装着“豆腐”。晌午时分,大家一哄而散,往家里跑。
一到家往厨房里冲,瞧见母亲架起柴火熬猪骨汤,锅里放入桂枝和姜片;熬得汤里有黄油浮在上面的时候,再放入切成小正方形的豆腐一起熬;熬到豆腐变大浮上来,就可以大快朵颐。呼啦呼啦,吃得真是爽。一大海碗吃下来,浑身发热,额头冒汗。“阿囡,慢慢吃,不要呛到。”慈祥的祖母笑眯眯地说。“过完年后,你们要打拼读书,争取考一百分。明年的年兜,就让你们吃排骨炖豆腐。”往往在这个时候,父亲“美丽的谎言”又来了。我们兄弟姐妹真会吃,可吃三大海碗猪骨豆腐汤。眼看汤少了,母亲就加一点水,再熬。但总是豆腐多猪骨少,直到汤由黄变清,味道由酽变淡才罢休,父亲戏之为“永不消逝的猪骨豆腐汤。”
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石磨已退出历史的舞台。想吃豆腐的话,网上一点,豆腐送到家。而那带着柴火味的老家豆腐时常进入我的梦境,暖到心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