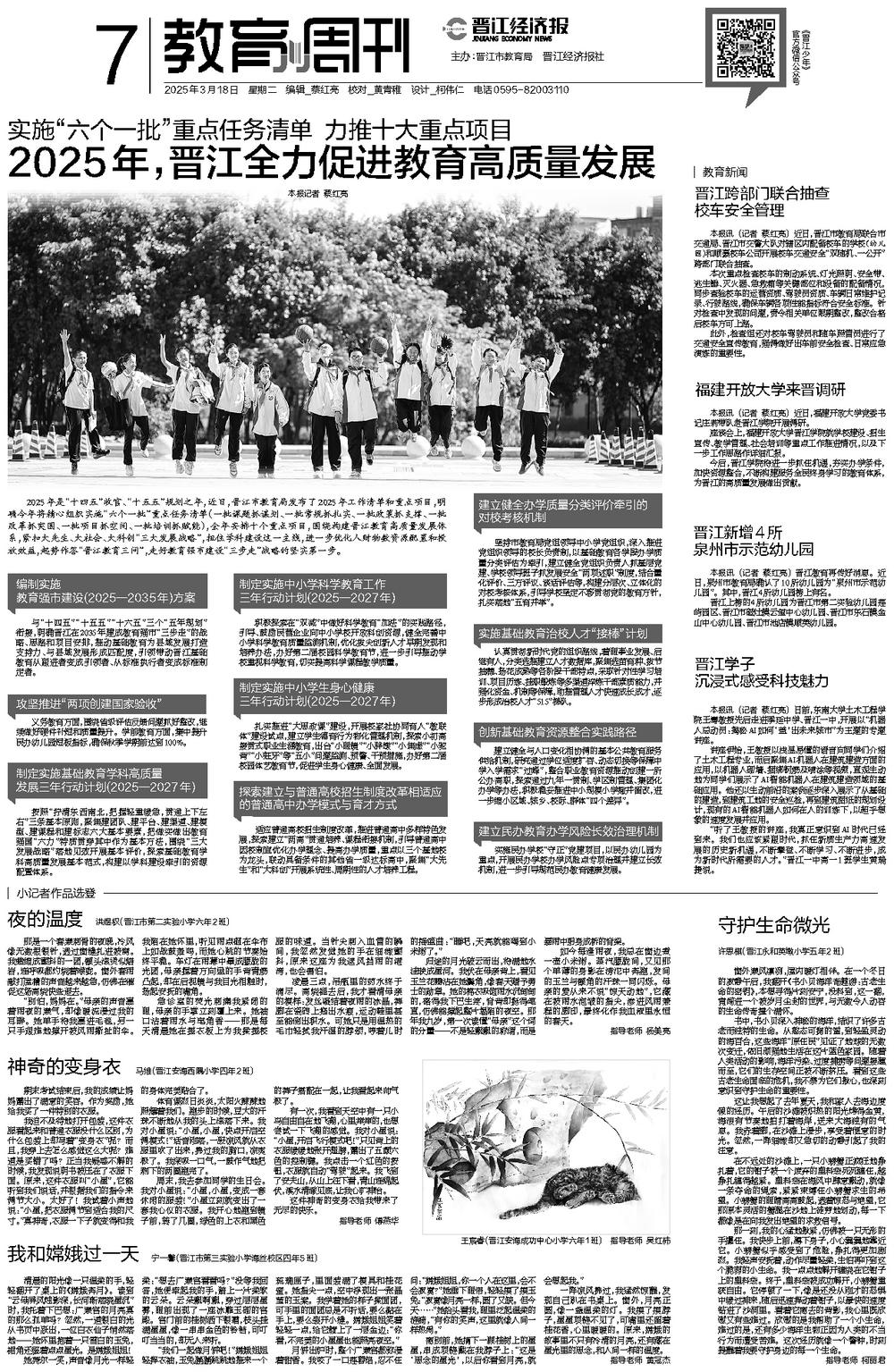洪煜权(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六年2班)
那是一个春寒刺骨的夜晚,冷风像无数根银针,透过窗缝扎进被窝。我蜷缩成颤抖的一团,额头滚烫似熔岩,连呼吸都灼烧着喉咙。窗外春雨敲打屋檐的声音越来越急,仿佛在催促这场高烧快些退去。
“别怕,妈妈在。”母亲的声音裹着雨夜的寒气,却像暖流漫过我的耳畔。她单手将我裹进毛毯,另一只手艰难地撑开被风雨撕扯的伞。我陷在她怀里,听见雨点砸在伞布上如战鼓轰鸣,而她心跳的节奏始终平稳。车灯在雨幕中晕成朦胧的光团,母亲握着方向盘的手背青筋凸起,却在后视镜与我目光相触时,扬起安抚的嘴角。
急诊室的荧光刺痛我紧闭的眼,母亲的手掌立刻覆上来。她袖口沾着雨水与皂角香——那是每天清晨她在搓衣板上为我揉搓校服的味道。当针尖刺入血管的瞬间,我忽然发觉她的手在细微颤抖,原来这座为我遮风挡雨的港湾,也会害怕。
凌晨三点,吊瓶里的药水终于滴尽。高烧褪去后,我才看清母亲的模样:发丝凝结着夜雨的冰晶,裤脚在瓷砖上拖出水痕,运动鞋里甚至能倒出积水。可她只是用温热的毛巾轻拭我汗湿的脖颈,哼着儿时的摇篮曲:“睡吧,天亮就能喝到小米粥了。”
归途的月光破云而出,将满地水洼映成星河。我伏在母亲背上,看见玉兰花瓣沾在她鬓角,像春天赠予勇士的勋章。她的棉衣吸饱雨水沉甸甸的,硌得我下巴生疼,脊背却挺得笔直,仿佛能撑起整片塌陷的夜空。那年我九岁,第一次读懂“母亲”这个词的分量——不是轻飘飘的称谓,而是暴雨中躬身成桥的脊梁。
如今每逢雨夜,我总在窗边煮一壶小米粥。蒸汽朦胧间,又见那个单薄的身影在滂沱中奔跑,发间的玉兰与额角的汗珠一同闪烁。母亲的爱从来不说“惊天动地”,它藏在被雨水泡皱的指尖,渗进风雨兼程的脚印,最终化作我血液里永恒的春天。
指导老师 杨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