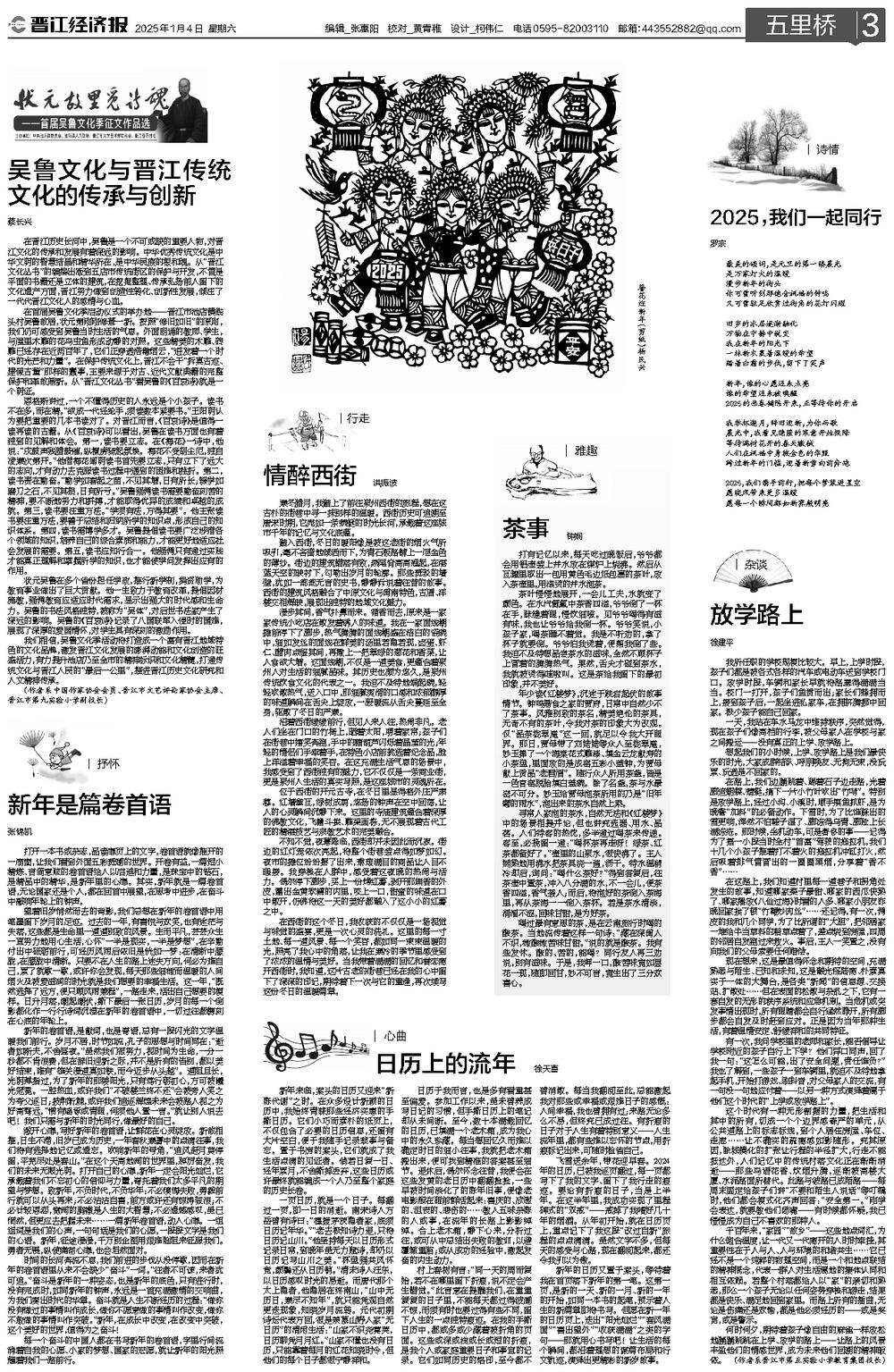徐建平
我所任职的学校规模比较大。早上,上学时段,孩子们都是被各式各样的汽车或电动车送到学校门口。放学时段,车辆和家长早就将路塞得满满当当。校门一打开,孩子们鱼贯而出;家长们蜂拥而上,接到孩子后,一起坐进私家车,在拥挤腾挪中回家。极少孩子能自己回家。
一天,我站在车水马龙中维持秩序,突然觉得,现在孩子们像高档的行李,被父母家人在学校与家之间搬运——没有真正的上学、放学路上。
想起我们的小时候,上学、放学路上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大家成群结队、呼朋唤友、无拘无束,没玩累、玩透是不回家的。
在路上,我们边蹦跳着、踢着石子边走路,光着脚追蝴蝶、蜻蜓,摘下一片小竹叶吹出“竹哨”。特别是放学路上,经过小沟、小溪时,顺手摸鱼抓虾,是为晚餐“加料”的必备动作。下雪时,为了比谁踩出的雪更响,浑然不怕鞋子湿了、脚冻得乌青、脚趾上长满冻疮。那时候,坐机动车,可是奢侈的事——记得为了搭一小段当时全村“首富”驾驶的拖拉机,我们十几个小孩子推着打不着火的拖拉机冲缸打火,然后吸着排气管冒出的一圈圈黑烟,分享着“香不香”……
在这路上,我们知道村里每一道巷子和拐角处发生的故事,知道哪家梨子最甜、哪家的西瓜快熟了、哪家播放《八仙过海》时看的人多、哪家小朋友昨晚回家挨了顿“竹鞭炒肉丝”……还记得,有一次,调皮的我和几个同学,为了比所谓的“大胆”,把邻居家一堆给牛当草料的稻草点着了,差点烧到房屋,四周的邻居自发跑过来救火。事后,主人一笑置之,没有向我们的父母索要任何赔偿。
现在想来,这是最值得怀念和期待的空间,充满熟悉与陌生、已知和未知,这是融光怪陆离、朴素真实于一体的大舞台,是各类“新闻”的信息源、交换站、扩散处……但在表面的松散与杂乱之下,它有一套自发的无形的秩序系统和应急机制。当危机或突发事情出现时,所有眼睛都会自行猛然睁开,所有脚步都会自发及时赶到应对。正是因为当年那种生活,有着温情安定、舒缓祥和的共同特征。
有一次,我问学校里的老师和家长,能否倡导让学校附近的孩子自行上下学?他们异口同声,回了我一句:“这怎么可能,出了安全问题,责任谁负?” 我也了解到,一些孩子一到车辆里,就迫不及待地拿起手机,开始打游戏、刷抖音,对父母家人的交流,有一句没一句地应付着——以另一种方式演绎着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上学或放学路上”。
这个时代有一种无形割据的力量,把生活和其中的所有,切成一个个边界感森严的单元,从公共道路上的标志标线,到个人居住房屋、车位、走廊……让不确实的疏离感如影随形。究其原因,除城镇化的扩张让行程的半径扩大,行走不能抵达外,人们记忆中的传统村落文化正在渐渐消逝——那些鸟语花香、炊烟升腾,逐渐被高楼大厦、水泥路面所替代。此路与彼路已成陌路——每周末固定给孩子们讲“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等叮嘱时,他们都会模式化齐声回答:“安全第一。”刚学会表达,就要教他们闭嘴——有时候都怀疑,我已慢慢成为自己不喜欢的那种人。
千百年来,“家园”“故乡”——这些地点词汇,为什么饱含温度,让一代又一代离开的人时时牵挂,其重要性在于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它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物理空间,而是一个和地点联结的精神概念,代表一群人对生活属地的集体认同和相互依赖。若整个村落都给人以“家”的亲切和熟悉,那么一个孩子无论以任何姿势穿梭和游走,结果都是快乐、满足地回到家里。而路上所有的插曲,无论是伤痛还是欢愉,都是他必须经历的——或是奖赏,或是警示。
何时何夕,期待着孩子像自由的麻雀一样放松地蹦蹦跳跳在上学、放学的路上——让路上的风景丰盈他们的情感世界,成为未来他们回溯的精神皈依。(作者系晋江市第五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