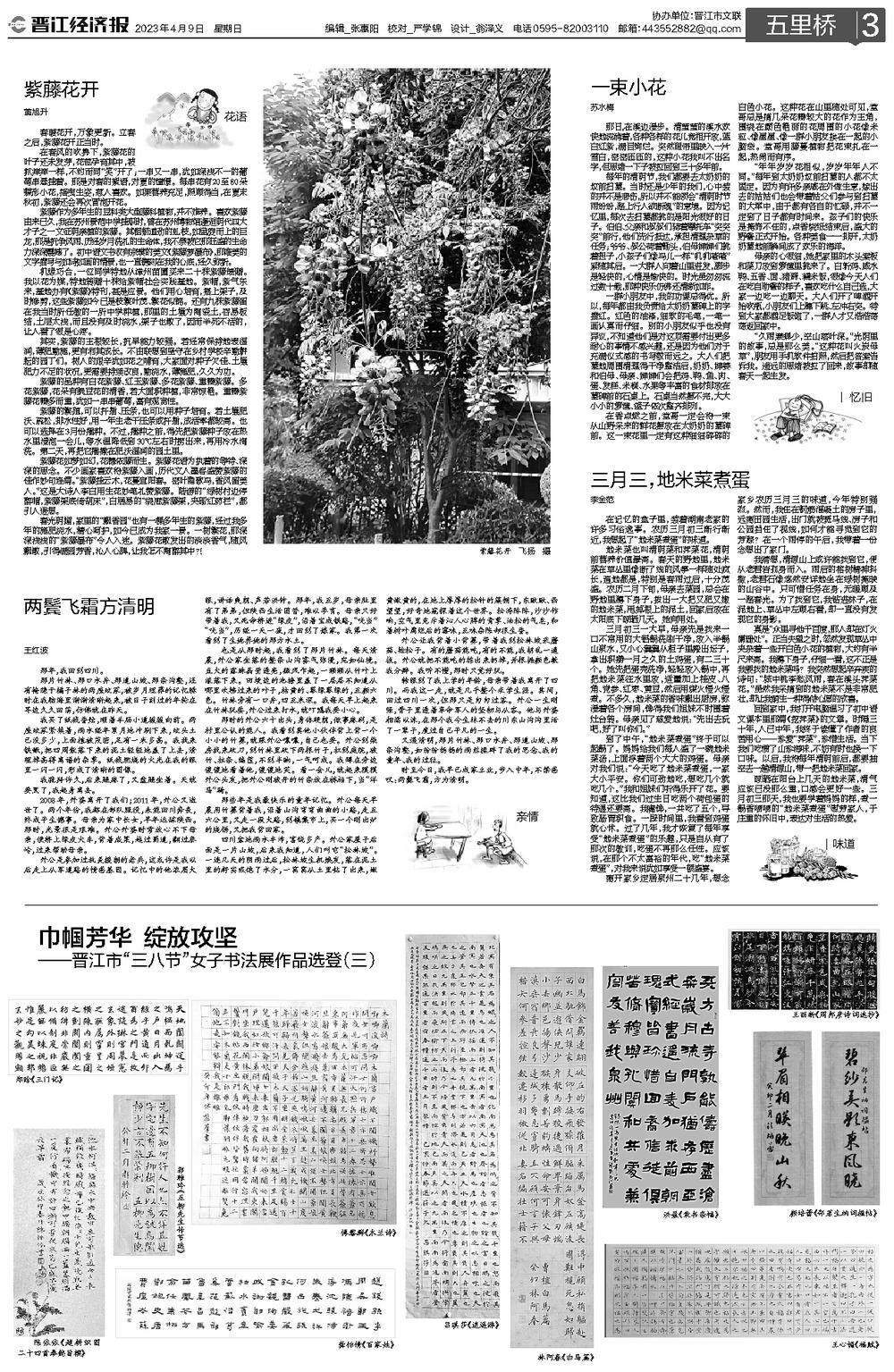王红波
那年,我回到四川。
那片竹林、那口水井、那道山坡、那条沟壑,还有掩隐于橘子林的两座坟冢,被岁月埋葬的记忆瞬时在我脑海里渐渐清晰起来,被日子刻过的年轮在耳边久久回荡,仿佛就在昨天。
我买了纸钱香烛,顺着羊肠小道缓缓向前。两座坟冢紧挨着,雨水经年累月地冲刷下来,坟头土已没多少,上面植被茂密,足有一米多高。我找来铁锹,把四周散落下来的泥土轻轻地盖了上去,清理掉高得离谱的杂草。纸钱燃烧的火光在我的眼里一闪一闪,形成了清晰的图像。
我跪拜许久,后来腿麻了,又盘腿坐着。天就要黑了,我起身离去。
2008年,外婆离开了我们;2011年,外公又逝世了。两个年份,我都在部队服役,未能回川奔丧,终成平生憾事。母亲为家中长女,早年远嫁陕西。那时,光景很是艰难。外公外婆时常放心不下母亲,便挤上绿皮火车,背着咸菜,越过蜀道,翻过秦岭,过来帮助母亲。
外公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这或许是我以后走上从军道路的情感基因。记忆中的他浓眉大眼,讲话爽朗、声若洪钟。那年,我五岁,母亲肚里有了弟弟,但陕西生活困苦,难以孕育。母亲只好带着我,又死命挤进“绿皮”,沿着宝成铁路,“咣当”“咣当”,历经一天一夜,才回到了娘家。我第一次看到了生她养她的那方水土。
也是从那时起,我看到了那片竹林。每天清晨,外公家坐落的整条山沟雾气弥漫,宛如仙境。豆大的露珠晶莹透亮,微风乍起,一颗颗从竹叶上滚落下来。田埂边的池塘里盖了一层层不知道从哪里吹拂过来的叶子,枯黄的、翠绿翠绿的,五颜六色。竹林旁有一口井,四五米深。我每天早上起来在竹林玩耍,外公过来打水,就叮嘱我要小心。
那时的外公六十出头,身体硬朗,做事麻利,是村里公认的能人。我看到其他小伙伴背上背一个小小的竹篓,就跟外公嚷嚷,自己也要。外公到柴房找来砍刀,到竹林里砍下两根竹子,扛到庭院,破竹、拉条、编筐,不到半晌,一气呵成。我蹲在旁边傻傻地看着他,傻傻地笑。看一会儿,就起来摸摸外公头发,把外公刚破开的竹条放在裤裆下,当“洋马”骑。
那些年是我最快乐的童年记忆。外公每天早晨用竹篓背着我,沿着山沟弯弯曲曲的小路,走五六公里,又走一段大路,到镇集市上,买一个刚出炉的烧饼,又把我背回家。
四川盆地雨水丰沛,富饶多产。外公家屋子后面是一片山坡,后来我知道,人们叫它“松林坡”。一连几天的阴雨过后,松林坡生机焕发,落在泥土里的籽实吸饱了水分,一窝窝从土里钻了出来,嫩黄嫰黄的,在地上厚厚的松针的簇拥下,东瞅瞅、西望望,好奇地窥探着这个世界。松涛阵阵,沙沙作响,空气里充斥着沁人心脾的青草、油松的气息,和着树叶腐烂后的霉味,五味杂陈却很生香。
外公让我背着小背篓,带着我到松林坡采蘑菇、捡松子。有的蘑菇能吃,有的不能,我胡乱一通拔。外公就把不能吃的拣出来扔掉,并根据颜色教我分辨。我听不懂,那时只觉好玩。
转眼到了我上学的年龄,母亲带着我离开了四川。而我这一走,就是几乎整个求学生涯。其间,回过四川一次,但那只是匆匆过客。外公一生刚强,骨子里透着革命军人的坚韧与从容。他与外婆相濡以沫,在那个我今生抹不去的川东山沟沟里活了一辈子,度过自己平凡的一生。
又遇清明,那片竹林、那口水井、那道山坡、那条沟壑,如纷纷扬扬的雨丝揉碎了我的思念、我的童年、我的过往。
时至今日,我早已成家立业,步入中年,不禁感叹:两鬓飞霜,方为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