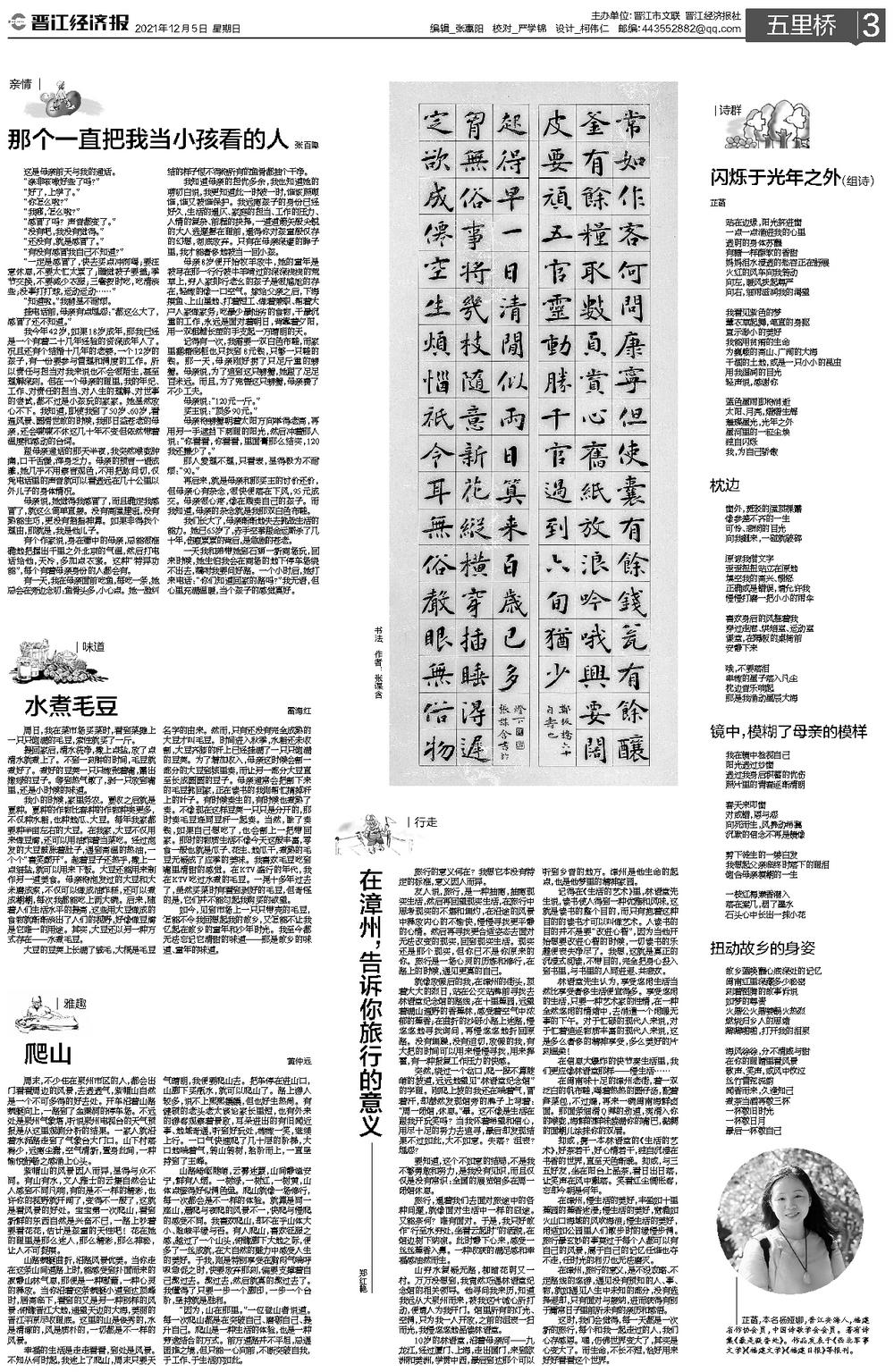张百隐
这是母亲前天与我的通话。
“涤非咳嗽好些了吗?”
“好了,上学了。”
“你怎么啦?”
“我哪,怎么啦?”
“感冒了吗?声音都变了。”
“没有吧,我没有觉得。”
“还没有,就是感冒了。”
“有没有感冒我自己不知道?”
“一定是感冒了,快去买点冲剂喝;要注意休息,不要太忙太累了;睡觉被子要盖;季节交换,不要减少衣服;三餐按时吃,吃清淡些;没事打打球,运动运动……”
“知道啦。”我稍显不耐烦。
挂电话前,母亲有点埋怨:“都这么大了,感冒了还不知道。”
我今年42岁,如果18岁成年,那我已经是一个有着二十几年经验的资深成年人了。况且还有个结婚十几年的老婆,一个12岁的孩子,有一份要参与管理和调度的工作。所以责任与担当对我来说也不会很陌生,甚至理解深刻。但在一个母亲的眼里,我的年纪、工作、对责任的担当、对人生的理解、对世事的尝试,都不过是小孩玩的家家。她显然放心不下。我知道,即使我到了50岁、60岁,看遍风景、圆滑世故的时候,我那日益苍老的母亲,还会喋喋不休这几十年不变但依然带着温度和感动的台词。
跟母亲通话的那天半夜,我突然喉咙肿痛,口干舌燥,浑身乏力。母亲的预言一语成谶,她几乎不用察言观色,不用把脉问切,仅凭电话里的声音就可以看透远在几十公里以外儿子的身体情况。
母亲说,她觉得我感冒了,而且确定我感冒了,就这么简单直接。没有高屋建瓴,没有熟能生巧,更没有掐指神算。如果非得找个理由,那就是,我是他儿子。
有个作家说,身在蜀中的母亲,总能很准确地把握出千里之外北京的气温,然后打电话给他,天冷,多加点衣裳。这种“特异功能”,每个有着母亲身份的人都会有。
有一天,我在母亲面前吃鱼,每吃一条,她总会在旁边念叨:鱼骨头多,小心点。她一脸纠结的样子恨不得将所有的鱼骨都抽个干净。
我知道母亲的担忧多余,我也知道她的唠叨白说,我更知道此一时彼一时,谁该照顾谁,谁又被谁保护。我远离孩子的身份已经好久,生活的逼仄、家庭的担当、工作的压力、人情的复杂、前程的抉择,一道道箭矢般尖锐的大人选题摆在眼前,逼得你对孩童般仅存的幻想,彻底放弃。只有在母亲深邃的眸子里,我才能奢侈地被当一回小孩。
母亲8岁便开始牧羊放牛,她的童年是被写在那一行行被牛羊啃过的深深浅浅的荒草上,穷人家排行老幺的孩子是很尴尬的存在,轻微的像一口空气。嫁给父亲之后,下海摸鱼、上山垦地、打着短工、做着兼职、帮着大户人家做家务;吃最少最拙劣的食物,干最沉重的工作,永远是面对着朝日,背靠着夕阳,用一双粗糙长茧的手支起一方晴朗的天。
记得有一次,我需要一双白色布鞋,而家里翻箱倒柜也只找到8元钱,只够一只鞋的钱。那一天,母亲刚好捞了只足斤重的螃蟹。母亲说,为了追到这只螃蟹,她跟了足足百米远。而且,为了兜售这只螃蟹,母亲费了不少工夫。
母亲说:“120元一斤。”
买主说:“顶多90元。”
母亲将螃蟹朝着太阳方向举得老高,再用另一手遮挡下刺眼的阳光,然后冲着那人说:“你看看,你看看,里面膏那么结实,120我还嫌少了。”
那人爱理不理,只看表,显得极为不耐烦:“90。”
再后来,就是母亲和那买主的讨价还价,但母亲心有杂念,很快便落在下风,95元成交。母亲很心疼,像在贱卖自己的孩子。而我知道,母亲的杂念就是我那双白色布鞋。
我们长大了,母亲渐渐地失去挑战生活的能力。她已65岁了,赤手空拳跟命运厮杀了几十年,伤痕累累的背后,是急剧的苍老。
一天我和弟带她到石狮一新商场玩,回来时候,她生怕我会在商场的地下停车场绕不出去,嘱咐我要问好路。一个小时后,她打来电话:“你们知道回家的路吗?”我无语,但心里充满温暖,当个孩子的感觉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