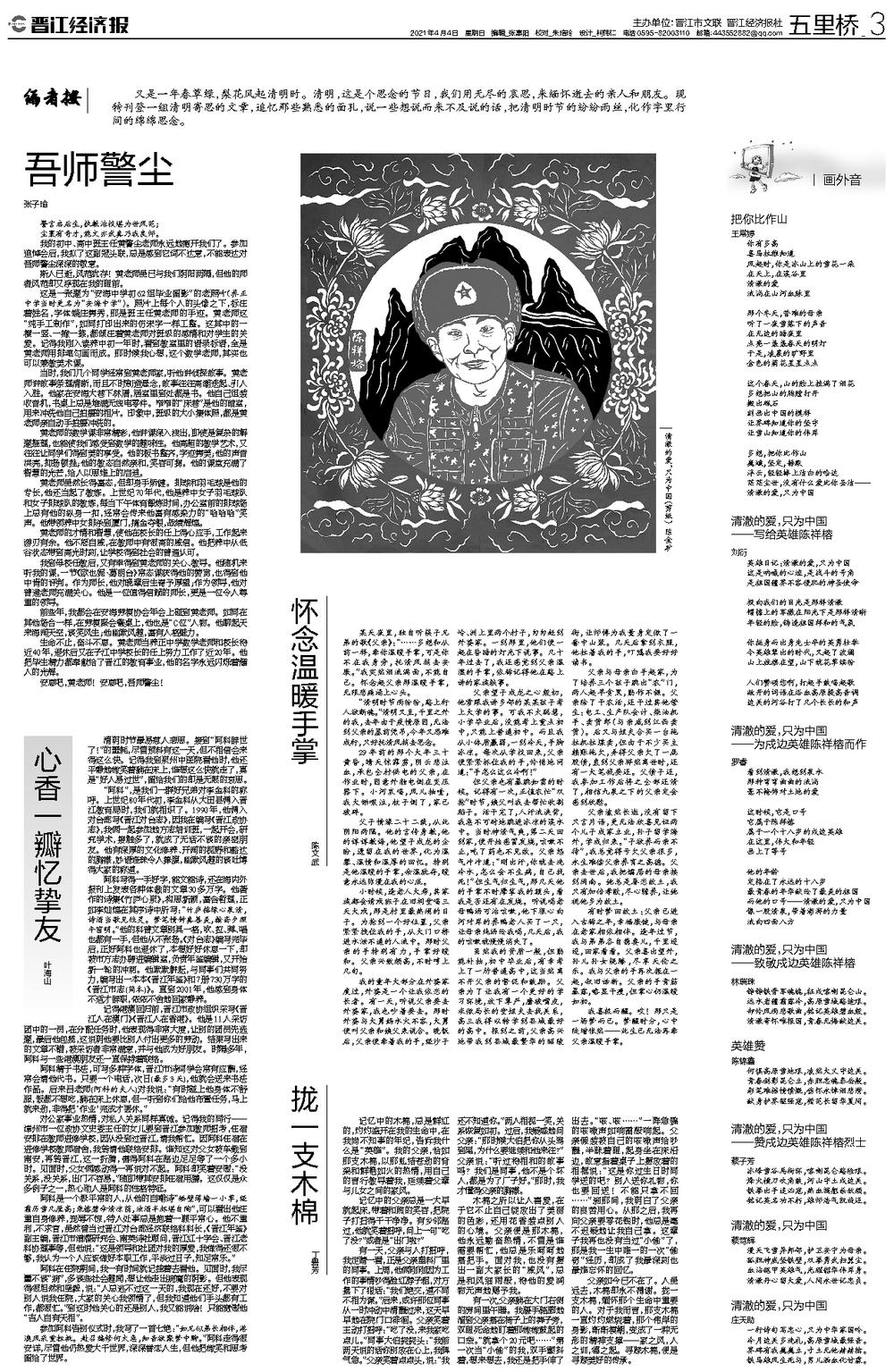叶海山
清明时节最易惹人悲思。接到“阿科辞世了!”的噩耗,尽管预料有这一天,但不相信会来得这么快。记得我到泉州中医院看他时,他还平静地微笑着躺在床上,谁想这么快就走了,真是“好人易过世”,留给我们的却是无限的哀思。
“阿科”,是我们一群好兄弟对李金科的称呼。上世纪80年代初,李金科从大田县调入晋江教育局时,我们就相识了。1990年,他调入对台部写《晋江对台志》,因我在编写《晋江政协志》,我俩一起参加地方志培训班,一起开会,研究学术,接触多了,就成了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他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开阔的视野和豁达的胸襟,妙语连珠令人捧腹,幽默风趣的谈吐博得大家的称道。
阿科写得一手好字,能文能诗,还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各种体裁的文章30多万字。他著作的诗集《竹庐心泉》,构思新颖,富含哲理,正如李灿煌在其序诗中所写:“竹庐摇绿心泉清,诗酒当歌见性灵。梦笔情钟真善美,翰斋夕照午窗明。”他的科普文章别具一格,吹、拉、弹、唱也都有一手,但他从不张扬。《对台志》编写完毕后,正好阿科也退休了,本想好好休息一下,却被市方志办聘进编辑室,负责年鉴编辑,又开始新一轮的冲刺。他默默耕耘,与同事们共同努力,编写出一本本《晋江年鉴》和7册730万字的《晋江市志(简本)》。直到2001年,他感到身体不适才辞职,依依不舍地回家静养。
记得港澳回归前,晋江市政协组织采写《晋江人在澳门》《晋江人在香港》。他是11人采访团中的一员,在分配任务时,他表现得非常大度,让别的团员先选题,最后他包揽,这说明他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劳动。结果写出来的文章不错,被采访者非常满意,并与他成为好朋友。时隔多年,阿科与一些港澳朋友还一直保持着联络。
阿科精于书法,可写多种字体,晋江市诗词学会常有应酬,经常会请他代书。只要一个电话,次日(最多3天),他就会送来书法作品。后来吕老师(阿科的夫人)对我说:“有时碰上他身体不舒服,饭都不想吃,躺在床上休息,但一听到你们给他布置任务,马上就来劲,非得把‘作业’完成才罢休。”
对公家事业热情,对私人关系同样真诚。记得我的同行——漳州市一位政协文史委主任的女儿要到晋江参加教师招考,住宿安排在教师进修学校,因从没到过晋江,请我帮忙。因阿科住宿在进修学校教师宿舍,我转请他联络安排。谁知这对父女被车载到南安,再转晋江,这一折腾,害得阿科在路边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见面时,父女俩感动得一再说对不起。阿科却笑着安慰:“没关系,没关系,出门不容易。”随即带其安排住宿用膳。这仅仅是众多例子之一,热心助人是阿科的性格特征。
阿科是一个极平常的人,从他的自嘲诗“矮壁薄墙一小草,经霜历雪几厘高;乘榕碧伞清凉荫,浊酒半杯堪自陶”,可以看出他注重自身修养,宠辱不惊,待人处事总是抱着一颗平常心。他不重利,不求官,虽然曾当过晋江对台部经济联络科科长,《晋江年鉴》副主编,晋江市谱牒研究会、南英诗社顾问,晋江红十字会、晋江老科协理事等,但他说:“这是领导和社团对我的厚爱,我做得还很不够,我认为一个人应该做好本职工作,平淡过日子,知足常乐。”
阿科在住院期间,我一有时间就记挂着去看他。见面时,我尽量不谈“病”,多谈些社会趣闻,想让他走出病魔的阴影。但他表现得很坦然和坚毅,说:“人总逃不过这一天的,我现在还好,不要对别人说我住院,大家的关心我领情了,但我知道他们手头都有工作,都很忙。”到这时他关心的还是别人,我又能说啥!只能宽慰他“吉人自有天相”。
参加阿科告别仪式时,我写了一首七绝:“如兄似弟长相伴,港澳风采重担挑。赴召编修何太急,知音欲聚梦中聊。”阿科走得很安详,尽管他仍热爱大千世界,深深眷恋人生,但他把微笑和思考留给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