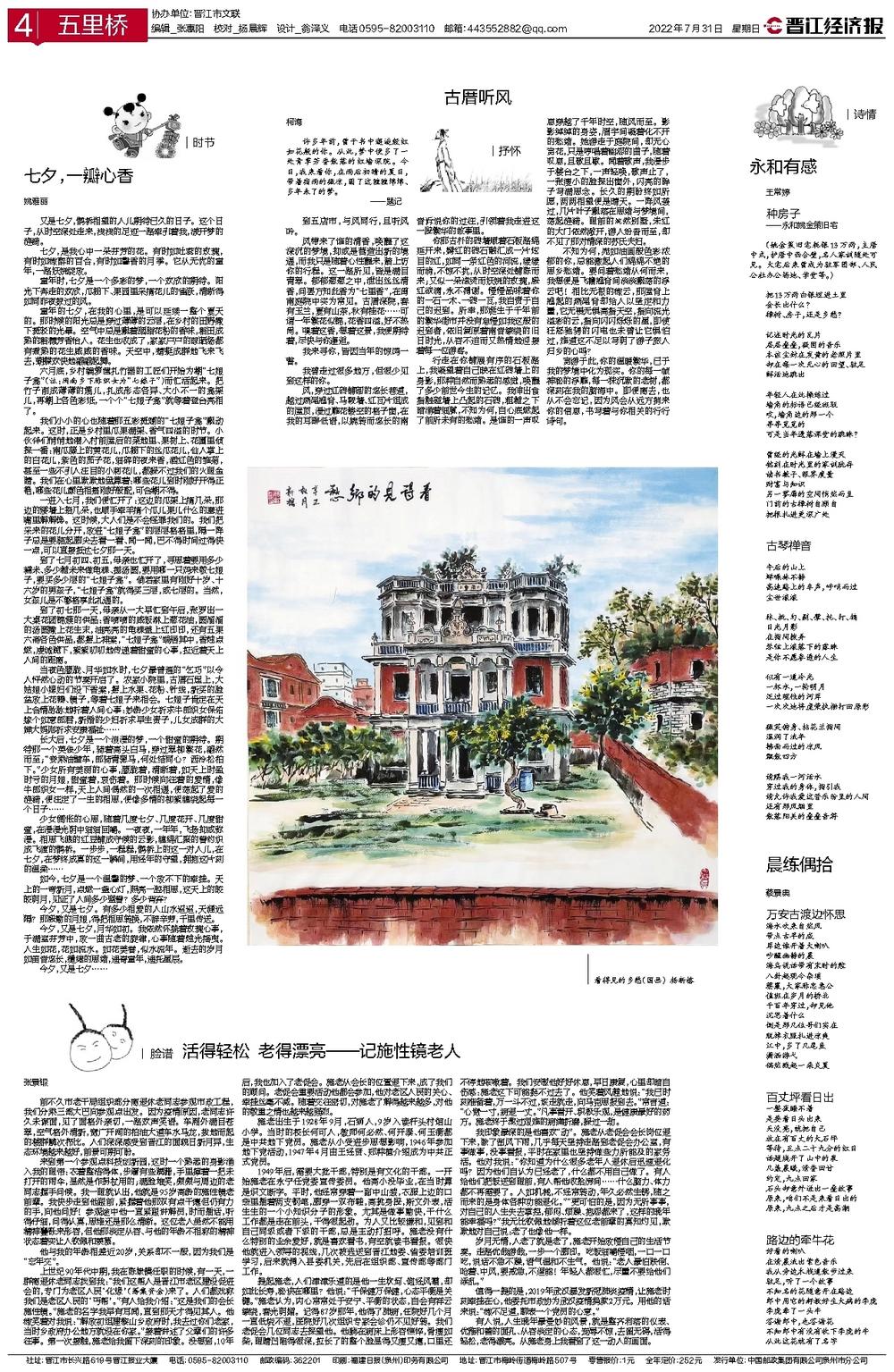张景锻
前不久市老干局组织部分离退休老同志参观市政工程,我们分乘三部大巴向参观点出发。因为疫情原因,老同志许久未谋面,见了面格外亲切,一路欢声笑语。车厢外满目苍翠,空气格外清新,宽广开阔的柏油大道车水马龙,拔地而起的楼群鳞次栉比。人们深深感受到晋江的面貌日新月异,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前景可期可盼。
来到第一个参观点科技创新园,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涌入我的眼帘:衣着整洁得体,步履有些蹒跚,手里撑着一把未打开的雨伞,显然是作拐杖用的;满脸堆笑,频频与周边的老同志握手问候。我一眼就认出,他就是95岁高龄的施性镜老前辈。我快步走到他跟前,紧握着他那双有点干瘪但仍有力的手,向他问好!参观途中他一直紧跟讲解员,时而插话,听得仔细,问得认真,思维还是那么清晰。这位老人虽然不能用精神矍铄来形容,但他那淡定从容、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精神状态着实让人钦佩和羡慕。
他与我的年龄相差近20岁,关系却不一般,因为我们是“忘年交”。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陈埭镇任职的时候,有一天,一群离退休老同志找到我:“我们这帮人是晋江市老区建设促进会的,专门为老区人民‘化缘’(筹集资金)来了。人们都戏称我们是老区人民的‘丐帮’。”有人给我介绍:“这是我们的会长施性镜。”施老的名字我早有耳闻,直到那天才得见其人。他微笑着对我说:“解放初组建黎山乡政府时,我去过你们老家,当时乡政府办公地方就设在你家。”接着讲述了父辈们的许多往事。第一次接触,施老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没想到,10年后,我也加入了老促会。施老从会长的位置退下来,成了我们的顾问。老促会重要活动他都会参加,他对老区人民的关心、牵挂丝毫不减。随着交往密切,对施老了解得越来越多,对他的敬重之情也越来越强烈。
施老出生于1928年9月,石狮人,9岁入读杆头村馆山小学。当时的校长何可人,教师何必然、何开泰、何玉衡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施老从小受进步思想影响,1946年参加地下党活动,1947年4月由王经贤、郑种植介绍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1949年后,需要大批干部,特别是有文化的干部。一开始施老在永宁任党委宣传委员。他高小没毕业,在当时算是识文断字。平时,他经常穿着一副中山装,衣服上边的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脚穿一双布鞋,高挑身段,斯文外表,活生生的一个小知识分子的形象。尤其是做事勤快,干什么工作都是走在前头,干得很起劲。为人又比较谦和,见到和自己同级或者下级的干部,总是主动打招呼。施老没有什么特别的业余爱好,就是喜欢看书,有空就读书看报。很快他就进入领导的视线,几次被选送到晋江地委、省委培训班学习,后来就调入县委机关,先后在组织部、宣传部等部门工作。
提起施老,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一生坎坷、饱经风霜,却如此长寿,秘诀在哪里?他说:“千保健万保健,心态平衡是关键。”施老认为,内心常常处于安宁、平衡的状态,自会有祥云缭绕,春光明媚。记得87岁那年,他得了肺病,住院好几个月一直低烧不退,医院好几次组织专家会诊仍不见好转。我们老促会几位同志去探望他。他躺在病床上形容憔悴,骨瘦如柴,眼睛凹陷得很深,拉长了的整个脸显得又瘦又瘪,口里还不停地咳嗽着。我们安慰他好好休息,早日康复,心里却暗自伤感:施老这下可能挺不过去了。他笑着风趣地说:“我已时刻准备着,万一斗不过,该走就走,向马克思报到去。”常言道:“心宽一寸,病退一丈。”凡事看开、积极乐观,是健康最好的药方。施老终于熬过艰难的病痛折磨,躲过一劫。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喜欢“动”。施老从老促会会长岗位退下来,除了刮风下雨,几乎每天坚持走路到老促会办公室,有事做事,没事看报,平时在家里也坚持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他对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很多老年人退休后迅速退化吗?因为他们自认为已经老了,什么都不用自己做了。有人给他们把饭送到眼前,有人帮他收拾房间……什么脑力、体力都不再需要了。人如机械,不经常转动,年久必然生锈,随之而来的是身体各种功能退化。”“更可怕的是,因为无所事事,对自己的人生失去掌控,郁闷、烦躁、抱怨都来了,这样的晚年能幸福吗?”我无比钦佩地倾听着这位老前辈的真知灼见,默默地对自己说:老了也像他一样。
岁月无情,人老了就是老了,施老开始放慢自己的生活节奏。走路优哉游哉,一步一个脚印。吃饭细嚼慢咽,一口一口吃,说话不急不躁,语气温和不生气。他说:“老人最怕跌倒、呛着、中风,要戒急,不逞能!年轻人都很忙,尽量不要给他们添乱。”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武汉暴发新冠肺炎疫情,让施老时刻牵挂在心,他委托市政协为武汉疫情捐款2万元。用他的话来说:“微不足道,聊表一个党员的心意。”
有人说,人生晚年最曼妙的风景,就是整齐利落的仪表、优雅和善的面孔、从容淡定的心态,宠辱不惊,去留无碍,活得轻松,老得漂亮。从施老身上我看到了这一动人的画面。